自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断言上古三代“茫昧无稽”开始,摆脱经学的羁绊,重新诠释上古史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各派争论和争夺的焦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上古史的诠释更是关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和革命前途的定位。虽然各派学者存在诸多分歧,但都趋向于把家族视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在采借西方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中国家族时,许多学者侧重于从血缘纽带和父权制入手去理解中国家族和古代社会的性质。其思想资源主要基于梅因的《古代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循此对中国古代社会展开诠释,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客观认识涂尔干学派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不过,我们今天却忽略了当时在社会学中还存在着另一条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路,即借助涂尔干学派的氏族图腾制理论,从家族内部的各种祭祀活动入手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当时,社会学(包括民族学或人类学)继史学和文学之后,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构建工作的主战场。翻检当时学院社会学的草创者,不难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宗侗(玄伯)、徐益棠、凌纯声、杨成志、卫惠林、杨堃、柯象峰和胡鉴民,大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留学法国,特别是在巴黎大学学习过民族学。其中,徐益棠、凌纯声和杨堃等人更是从学于涂尔干的学生莫斯。当时在法国教育界和学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涂尔干学派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倾向于把“涂尔干的年鉴学派”等同于唯一的“法国社会学派”。或许是受到莫斯等人重视资料收集这一研究取向的影响,上述留法学者归国后开展的民族学研究非常重视“现象的罗列”,并不容易看出涂尔干学派的理论痕迹。因此,长期以来,国内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倾向于认为凌纯声、杨成志、徐益棠和杨堃等“法国民族学派”并没有应用法国民族学的观点。 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下述事实及其理论意义:这批赴法学习民族学的研究者所开展的各项研究,特别是李宗侗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初民社会》、卫惠林的《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杨堃的《灶神考》《女娲考》、凌纯声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台湾土著族的宗庙与社稷》《中国祖庙的起源》《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和《中国古代社之源流》,都动用了共同的思想资源(即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家族和古代社会,其焦点则在于各种宗教崇拜,如社神崇拜、灶神崇拜、祖先崇拜、昭穆制、姓和婚姻制度。 涂尔干学派当时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还延伸至史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王静如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中曾指出,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徐炳昶和林语堂等人的研究都受到法国汉学影响,且“是中国学者已有渐由‘史语方法’而向‘社会科学方法’途径上迈进之势”。后者的代表正是涂尔干学派,尤其是葛兰言的汉学研究。倘若他所言不虚,那么涂尔干学派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显然被低估了。今天的史学界,虽然对上古史和辽金元等民族史中的图腾泛滥说多有批评,但却没有人留意到其思想源头可能正是涂尔干学派的氏族图腾制理论。 重视亲属关系在人类社会组织中的作用 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在当时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首先要回到涂尔干本人所处的学术脉络中。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梅因、库朗热、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恩格斯等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受普遍历史观和进化论的影响,都把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初民社会”或“原始社会”,作为认识西方文明特别是史前时期“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参照。非西方文明(如澳洲、美洲、印度和中国)被欧洲人发现之前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被看作西方文明曾经历过的类似阶段,尤其是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建立之前的社会形态。史前时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乏,给民族学和社会学有关古代社会的诠释留下了极大的理论想象空间和发挥空间。继梅因、库朗热的父权论,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的母权论之后,涂尔干把图腾崇拜视为理解古代社会组织,特别是亲属关系的核心。 在19世纪中叶之前,每个人都确信父亲是家庭中的本质要素,我们都没有设想过存在某种家庭组织,在那里父权竟然不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巴霍芬的发现却推翻了这个陈旧的观念……巴霍芬及其后继者麦克伦南、摩尔根等人仍然处于这一偏见的影响之下。然而,由于我们已经了解到原始氏族的本性,我们才知道,恰恰相反,亲属关系是不能借助血缘关系来定义的。(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把图腾宗教视作最为原始和最为简单的宗教形态,并据此来解释其他宗教乃至宗教信仰本身,并不始于涂尔干。后者的图腾制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基于图腾崇拜来解释氏族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在涂尔干看来,基于图腾崇拜建立的亲属关系,而非基于生理或种族建立的血缘关系,才是人类社会组织最为原始和最为基础的关系。 图腾制理论影响中国古代史建构 正是氏族图腾制理论的这一理论抱负,激起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者的兴趣。与西方学者援引澳洲和美洲的氏族来诠释希腊和罗马社会一样,李宗侗、凌纯声和杨堃等人认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一种“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其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遗痕”,因而是“研究中国古史活的史料”。因此,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辅之以新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对古史的溯源考证,不仅可以重新诠释中国上古社会,而且还可以重新厘定中国社会史分期,给出一部“中国通史”。 在李宗侗那里,祖先崇拜源自图腾崇拜,而“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在凌纯声那里,畲民的祖先崇拜也是一种图腾崇拜,在后者所开展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宗庙和社稷研究中,祭祖与祀神在最初是一回事,都源于原始人对男女性器官的图腾崇拜;在杨堃那里,中国家内的灶神崇拜,源自以蛙为图腾的民族的图腾崇拜……把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等都追溯到图腾崇拜,意味着中国上古社会存在某个阶段,家与国、祖先崇拜、社稷崇拜与图腾崇拜还未分开。在这个阶段,人们依靠图腾崇拜结成若干个原初的、混沌的氏族。无论是依靠血缘纽带所组建的家庭,还是已然存在首领的部落或国家,都是随后才从氏族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国家权力或君权并不源自父权,而是源自古老的图腾崇拜、源自某种“集体力”或“社会力”,因为图腾膜拜实际上是对氏族或社会本身的膜拜。 总之,受涂尔干学派氏族图腾制理论的启发,对中国家族内部各种宗教信仰和亲属制度等所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推断,都侧重于强调共同的信仰或文化而非血缘或种族关系在社会凝聚和民族构建上的重要性。如果父权并不构成国家权力的原型,而家族也不构成私有制、阶级压迫或国家的起源,那么家族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对其未来所作的展望就是另一幅图景。 因此,在上述研究者那些琐碎、细致甚至牵强的事实罗列和古史考证背后,隐含着的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中家与国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借助社会学研究来重新订定中国上古史、重构中华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演进的规范性冲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这一奠基性时刻又与宏观层面上中国近代从传统帝国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遥相呼应。可见,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对于理解和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制度而言,早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图腾制的理论,是否赞同中国早期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路径,我们在今天都无法轻易绕过这些理论而进入“中国”。
重视氏族图腾制视角下的家族研究
客观认识涂尔干学派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不过,我们今天却忽略了当时在社会学中还存在着另一条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路,即借助涂尔干学派的氏族图腾制理论,从家族内部的各种祭祀活动入手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当时,社会学(包括民族学或人类学)继史学和文学之后,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构建工作的主战场。翻检当时学院社会学的草创者,不难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宗侗(玄伯)、徐益棠、凌纯声、杨成志、卫惠林、杨堃、柯象峰和胡鉴民,大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留学法国,特别是在巴黎大学学习过民族学。其中,徐益棠、凌纯声和杨堃等人更是从学于涂尔干的学生莫斯。当时在法国教育界和学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涂尔干学派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倾向于把“涂尔干的年鉴学派”等同于唯一的“法国社会学派”。或许是受到莫斯等人重视资料收集这一研究取向的影响,上述留法学者归国后开展的民族学研究非常重视“现象的罗列”,并不容易看出涂尔干学派的理论痕迹。因此,长期以来,国内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倾向于认为凌纯声、杨成志、徐益棠和杨堃等“法国民族学派”并没有应用法国民族学的观点。
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下述事实及其理论意义:这批赴法学习民族学的研究者所开展的各项研究,特别是李宗侗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初民社会》、卫惠林的《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杨堃的《灶神考》《女娲考》、凌纯声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台湾土著族的宗庙与社稷》《中国祖庙的起源》《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和《中国古代社之源流》,都动用了共同的思想资源(即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家族和古代社会,其焦点则在于各种宗教崇拜,如社神崇拜、灶神崇拜、祖先崇拜、昭穆制、姓和婚姻制度。
涂尔干学派当时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还延伸至史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王静如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中曾指出,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徐炳昶和林语堂等人的研究都受到法国汉学影响,且“是中国学者已有渐由‘史语方法’而向‘社会科学方法’途径上迈进之势”。后者的代表正是涂尔干学派,尤其是葛兰言的汉学研究。倘若他所言不虚,那么涂尔干学派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显然被低估了。今天的史学界,虽然对上古史和辽金元等民族史中的图腾泛滥说多有批评,但却没有人留意到其思想源头可能正是涂尔干学派的氏族图腾制理论。
重视亲属关系在人类社会组织中的作用
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在当时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首先要回到涂尔干本人所处的学术脉络中。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梅因、库朗热、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恩格斯等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受普遍历史观和进化论的影响,都把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初民社会”或“原始社会”,作为认识西方文明特别是史前时期“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参照。非西方文明(如澳洲、美洲、印度和中国)被欧洲人发现之前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被看作西方文明曾经历过的类似阶段,尤其是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建立之前的社会形态。史前时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乏,给民族学和社会学有关古代社会的诠释留下了极大的理论想象空间和发挥空间。继梅因、库朗热的父权论,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的母权论之后,涂尔干把图腾崇拜视为理解古代社会组织,特别是亲属关系的核心。
在19世纪中叶之前,每个人都确信父亲是家庭中的本质要素,我们都没有设想过存在某种家庭组织,在那里父权竟然不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巴霍芬的发现却推翻了这个陈旧的观念……巴霍芬及其后继者麦克伦南、摩尔根等人仍然处于这一偏见的影响之下。然而,由于我们已经了解到原始氏族的本性,我们才知道,恰恰相反,亲属关系是不能借助血缘关系来定义的。(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把图腾宗教视作最为原始和最为简单的宗教形态,并据此来解释其他宗教乃至宗教信仰本身,并不始于涂尔干。后者的图腾制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基于图腾崇拜来解释氏族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在涂尔干看来,基于图腾崇拜建立的亲属关系,而非基于生理或种族建立的血缘关系,才是人类社会组织最为原始和最为基础的关系。
图腾制理论影响中国古代史建构
正是氏族图腾制理论的这一理论抱负,激起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者的兴趣。与西方学者援引澳洲和美洲的氏族来诠释希腊和罗马社会一样,李宗侗、凌纯声和杨堃等人认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一种“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其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遗痕”,因而是“研究中国古史活的史料”。因此,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辅之以新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对古史的溯源考证,不仅可以重新诠释中国上古社会,而且还可以重新厘定中国社会史分期,给出一部“中国通史”。
在李宗侗那里,祖先崇拜源自图腾崇拜,而“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在凌纯声那里,畲民的祖先崇拜也是一种图腾崇拜,在后者所开展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宗庙和社稷研究中,祭祖与祀神在最初是一回事,都源于原始人对男女性器官的图腾崇拜;在杨堃那里,中国家内的灶神崇拜,源自以蛙为图腾的民族的图腾崇拜……把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等都追溯到图腾崇拜,意味着中国上古社会存在某个阶段,家与国、祖先崇拜、社稷崇拜与图腾崇拜还未分开。在这个阶段,人们依靠图腾崇拜结成若干个原初的、混沌的氏族。无论是依靠血缘纽带所组建的家庭,还是已然存在首领的部落或国家,都是随后才从氏族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国家权力或君权并不源自父权,而是源自古老的图腾崇拜、源自某种“集体力”或“社会力”,因为图腾膜拜实际上是对氏族或社会本身的膜拜。
总之,受涂尔干学派氏族图腾制理论的启发,对中国家族内部各种宗教信仰和亲属制度等所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推断,都侧重于强调共同的信仰或文化而非血缘或种族关系在社会凝聚和民族构建上的重要性。如果父权并不构成国家权力的原型,而家族也不构成私有制、阶级压迫或国家的起源,那么家族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对其未来所作的展望就是另一幅图景。
因此,在上述研究者那些琐碎、细致甚至牵强的事实罗列和古史考证背后,隐含着的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中家与国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借助社会学研究来重新订定中国上古史、重构中华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演进的规范性冲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这一奠基性时刻又与宏观层面上中国近代从传统帝国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遥相呼应。可见,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对于理解和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制度而言,早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图腾制的理论,是否赞同中国早期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路径,我们在今天都无法轻易绕过这些理论而进入“中国”。
(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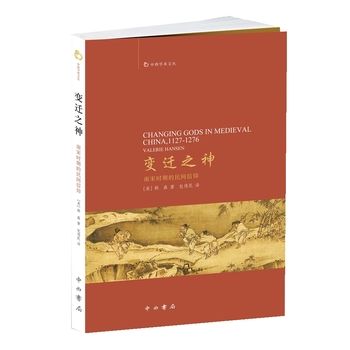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