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中国宗教研究来看,还是就中国文化传统研究而言,如何认识与评价“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堪称一个既复杂又严重的老大难问题。追究起来,所谓的“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早在明末清初,东西方文化传统的首次深层碰撞中就被西方传教士提出来了,他们可谓全盘否定中国民间信仰的始作俑者。而在此后百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经过数次重要论争,像“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是否应以科学、美育、道德或哲学来取代宗教”“儒家、儒学或儒教是否属于宗教或国教”等问题,不但变得愈加复杂且严重,甚至可以说,已到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决断的地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回到田野”,借助史料数据、特别是现状调研,切实感悟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研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问题的提出:让田野调查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曾共同组织实施“浙江民间信仰现状调研项目”。该项目堪称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当代民间信仰所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地域较广、内容较全的实地调研活动。此次调研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和民间文化工作者合作,调研地区主要选择温州市、台州市、义乌市等,调研内容广泛涉及民间信仰的神祇崇拜、祖先崇拜、仪式活动、五大宗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重点问题则聚焦于: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有效地管理民间信仰活动等。此次调研的大量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撰文予以评介,其提出的如下相关观点值得深思:
民间信仰现状及其主要特点。此次调研发现,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意指“五大宗教”,笔者注)相比,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数量大、规模小、参与信众广泛、管理形式多样等。例如,《关于浙江省台州市民间信仰状况和管理的调查报告》指出,当地的民间信仰现状可概括为3点:民间信仰的庙宇量多面广,星罗棋布,已成为村社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的神明崇拜和香火祭祀传统深厚,类型多样,已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当地,城隍、土地公、玉皇大帝、观音、天地水三官、关公、龙王等全国性神明崇拜普遍存在,白鹤大帝、济公、钱王、胡公、张元帅等地方性神明也有很大影响。民间信仰活动大多由当地精英牵头,群众热衷参与,已成为乡村自治的凝聚符号。由此可见,在民间信仰的复兴过程中,基层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基础,当地精英的策划组织是关键。
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以台州市为例,1996年以来,该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先后多次开展了未经审批小庙小庵整治工作,但整治效果并不理想。鉴于这种情况,台州市临海地区(县级市)有关部门从2004年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现已取得不少成果。主要经验包括:首先,对于民间信仰要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地方政府部门要认识到,民间信仰问题具有统战性、群众性、长期性等特点,要转变以往“只堵不疏”的管理思路,“疏堵结合,正面引导,规范管理,确保安全”;其次,对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要积极探索、敢于实践,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如纳入属地管理,明确管理主体;建立工作网络,形成“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的工作格局;制定管理制度,促使规范管理等。再次,面对民间信仰的现实存在,由“打击制止”转为“正面引导”,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问题,又消除了安全隐患,化解了群众抵触情绪,群众拥护配合,基层干部支持,真正落实管理措施。以上实践经验表明,做好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有利于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保护传统文化,平衡宗教生态,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
民间信仰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此次关于当代民间宗教现状的调研表明,如何从理论层面上来界定民间信仰,认清民间信仰的性质与作用,为民间信仰的正常发展与科学管理提供学理根据,是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金泽指出,民间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对于所谓的“民间信仰大复兴”(有些人称“死灰复燃”),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已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所处的时代,不但其外部环境变化了,如政治、经济、文化、城镇化进程、人口素质等,而且其内部结构与整体功能也不同于过去,并且还会随着社会转型而发展变化。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再生产,其未来发展和社会作用,既取决于文化传统,也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
上述理论思考并非只是根据浙江省的民间信仰现状调研。金泽指出,近些年来,有关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地区的民俗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的大量田野调查报告表明,民间信仰在整个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它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一些地区,无论从信众人数来看,还是从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上来说,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五大宗教”。因此,从当下中国宗教的发展态势和宗教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调动一定的学术资源,加强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其理由不仅仅在于民间信仰在我国的许多地区仍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活态文化现象,其活动场所多、信众广;更重要的是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作为“老百姓的信仰权利”,理应受到重视与尊重。况且过去统统被扣上“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如今其中的一些群体性的、敬天法祖的、崇贤尚德的、历史悠久的祭拜活动,已经有了“合法的地位”,这在理论与政策研究层面,都给我们提出了挑战。金泽指出:就调研成果而言,在“民间信仰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争议;对于“民间信仰的规模与范围”,虽然存在争论,但并不涉及“事实判断”,而属于“调查技术和预设尺度”问题;真正深层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即对民间信仰作出怎样的“价值判断”。有人认为,民间信仰是“草根文化”,是“文化遗产”,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本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尊重和宽容;但也有人认为,这在古代属于“淫祀”,在今天属于“封建迷信”,是“落后的、反科学的东西”,应该彻底否定。
中国民间信仰与价值判断问题
要对中国民间信仰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理应着眼于其主流与本质,这种方法论取向可使我们着重发掘其“真精神与正能量”,从而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引导中国民间信仰。这不但是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原则,即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与判断,均要注重其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性质、主要的作用等,而且我们应当据此来深刻地反省长期流行于中国民间信仰领域的两种偏颇的价值判断倾向。
一是把中国民间信仰一概看成是“迷信”。这种偏颇的成见最初来自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但我们至今尚需追究的是,为什么这种“西方的成见”竟会盛行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呢?综合的学术反省或许可使我们思索个中的复杂原因。即中国知识界的民间信仰研究发端于晚清时期的“批判迷信”,其目的就在于破除迷信、启蒙思想、改良社会等。因而,这一时期所用的“迷信”一词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批判倾向。如《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刊载的《续无鬼神演义》一文认为,中国民间的“种种迷信”导致“种灭国亡”。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俗学界才开始用“民俗”“俗信”或“民间信仰”等词,为相关研究内容脱敏;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又策略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为民间信仰研究“去污名化”。
二是把中国民间信仰简单地看成“民间宗教”,并将“民间宗教”主要解释为“民间教派”或“秘密宗教”等。如果说前一种价值判断倾向明显地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民间信仰”,那么,这种概念理解则会直接或间接地把民间信仰引向“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并由此导致片面的、甚至恶性的价值判断。正如有些学者指出,我国学术界早期的“民间教派”研究多采用“秘密宗教”概念,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间宗教”研究又集中关注“民间教派”,不少学者则将此延伸到“会道门、会党”研究。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首先遇到的仍是概念界定与定性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大都秘密流传,故把“民间宗教”称为“秘密宗教”“秘密教门”“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等。然而,从历史来看,并非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是“秘密的”、遭到取缔的。因此,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不能只从政治层面来加以界定,不能把“民间宗教”与“秘密宗教”“秘密结社”“农民起义”等混为一谈,因为后一类概念其实隐含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
在笔者看来,无论海内外的研究者如何界定中国历史上和现存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有一点乃是不争的事实,即所谓的“民间信仰”主要就是指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信奉的传统习俗。这里且不论近二三十年来的大量田野调查能否证实,中国基层社会现存的民间信仰形态在信众数量、分布范围、活动规模等方面是否都远远超过了几大体制性宗教;仅就“民间信仰主要是属于老百姓的传统习俗”这一点而言,我们是否就应该深刻地反省前述两种长期流行的价值判断倾向呢?若把“迷信、愚昧、落后”这顶大帽子全都扣在千千万万归属民间信仰的老百姓头上,或把研究目光主要盯在“秘密宗教、秘密教门、民间秘密结社”等少数民间异常现象那里,这些做法是否显然有悖于客观性、全面性、严谨性等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呢?当然,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林林总总的民间信仰当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甚至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然而,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传统,诸种本土的或外来的制度性宗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复杂作用岂不也是这样吗?一言以蔽之,以“主流与本质”作为价值判断的着眼点,这一方法论原则不但适用于制度性宗教研究,同样也适合于民间信仰研究。
当然,这里需要慎重说明,如果把“红军菩萨”“解放军庙”等划归“民间信仰”,大概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但若把此类现象视同“民间宗教”,则显然不够严谨或不太恰当。笔者将此类新现象引入学术讨论,主要是为了印证中国老百姓所普遍怀有的“崇德报功观念”。因为从历史学观念来看,此类新现象距离我们是“那么近”,是在我们身边“刚发生”的,所以我们不难调研清楚“其缘由”,即当地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感恩并祭祀“她(他)们”。在笔者看来,这里所例证的“缘由”,或许就是我们所要探究的中国老百姓信仰状况的“奥秘”之一,即中国本土民间信仰的底色、本性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
(作者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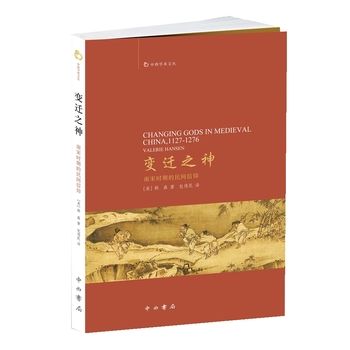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