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文化记忆的基石
高长江
浙江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文化记忆是一个共同体有关自我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理想等知识生产与传承的精神生活。因其记忆的信息既非个体生活史亦非普通社会史, 而是通过“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所创造的集体共享假设, 具有关于世界的公义与秩序、生命的尊严与幸福等“超越日常之上”的价值维度, 故它多以宗教类文化为承载形体。中国文化记忆亦与中国特有的宗教文化——民间信仰密切相关。中国民间信仰不仅因其记忆形象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气脉相通而传承着中国文化记忆, 而且它的运作机制、所使用的信息载体以及激活、唤醒文化记忆的积极过程, 也奠定了其中国文化记忆承载基石的地位。
关键词:
作者简介:高长江, 浙江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近年来, 有关文化记忆的话题悄然兴起, 并在文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领域相继膨胀话语空间。当代中国学界的这一“文化记忆”理论热, 也许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国内学人对海外学术思潮的追踪, 亦不完全似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扬·阿斯曼所解释的因那些历史重大事件见证人相继离世可能产生的历史记忆消失的恐惧反应, (1) 当然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系对当代中国“记忆文化”热 (2) 的理论回应。我认为, 其理论思维的语境乃是对当代社会所显现的文化记忆“集体失忆症”的忧虑以及重构中国文化记忆连续性的希冀。我这里所说的“集体失忆”, 指的是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史诗”的认同、信仰、记忆的衰颓。
一、文化记忆的特征与机制
在扬·阿斯曼所建构的文化记忆理论范型中, 人类的“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相对应:交往记忆系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 它“随着时间而产生并消失”;文化记忆的内容则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的记忆, 如犹太人关于圣祖的故事、出埃及、穿越沙漠、取得迦南的土地、流亡等都这样的形象, 它们具有“某种神圣的因素”即宗教因素。从时间结构上看, 交往记忆的时间上限为80年以内, 通常以40年为重要门槛;而文化记忆的时间可延展到神话性的史前时代。从回忆和叙事方式看, 交往记忆主要依凭口述史实, 但文化记忆则是通过在节日中以礼拜方式的展演, 于是, 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的历史, 从而变成了神话。鉴于文化记忆的内容、时间结构以及回忆的形式, 他得出结论说:交往记忆与文化回忆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生活”与“节日庆典”或“日常记忆”与“节日记忆”的区别。 (1)
应当承认, 阿斯曼从内容、时间与回忆形式等视阈对文化记忆内涵的厘定, 具有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里程碑意义。不过, 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把文化记忆的时间结构限定于“史前时代”, 这便等于把文化记忆等同于神话-宗教记忆;把记忆的媒介认定为文字和仪式, 这又与社会记忆、国家记忆等相互拉扯难以分离;特别是通过“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比照凸显文化记忆的特质更使“文化记忆”变得模糊难辨。诚然, 记忆, 作为漫步于这颗小行星上的高级灵长类动物独有的心智现象, 不仅如弗洛伊德所说, 是由“语境连绵的细节”缝合的信息网络, 很难切割出一个个边界清晰的信息模块, 而且其所依凭的数据载体亦非单一形式。但我相信, 只要选择一个合理的逻辑标尺, 我们是可以梳理出一个恰当的框架的。例如, 以记忆主体为视角, 可以把记忆分为国家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以记忆内容为视角, 又可把记忆分为自传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我的观点是, 以记忆主题、存储载体以及回忆风格为标准, 与文化记忆相对应的是自传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自传体记忆”是神经科学家所说的有机体关于“自传式自我”的记忆。与恩斯特·海克尔所说的“细胞记忆” (2) 不同, 它虽离不开对神经元的世俗依赖, 但更主要的是一种心理记忆。这种记忆属于“对一个有机体的过去经验的有组织记录”, 还包括“对未来的预见”, 是“关于我们的身体、心理和个人背景同一性的事实, 关于我们最近的行踪的事实, 以及我们在不久的未来马上就想做的事实” (3) 等的记忆。其信息存储主要是个体的神经网络系统;记忆调取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当环境数据输入刺激相应的神经节点, 某些记忆就可能复活:当我看到冰雪的画面或想到“雪”这个概念时, 我的脑海便浮现出长白山下的那个小镇和镇上那些熟悉的人和物的表象:茅屋、炊烟和包着围巾的圆脸姑妈等。 (4)
“社会记忆”是一个概念边界比较模糊、内涵闪烁不定的术语, 可以说骑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马头墙上, 界定起来相当困难, 但我认为它还可以是一个允许描述人类记忆现象的概念。彼得·伯克认为这种记忆的信息主要是社会史的范畴;哈拉尔德·韦尔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它属于“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的记忆 (5) 的界定。不难发现, 在韦尔策“社会记忆”的认知模型中, “社会”这个词既指称记忆主体, 又指涉信息类别。记忆主体与主题跨逻辑接合, 使得“社会记忆”的内涵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从记忆信息主题这个视角分析, 我比较认同伯克的观点, 社会记忆就是社会群体关于“社会史”方面信息的记忆, 内容主要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重大的事件。其信息承载的媒体主要系社会的信使系统, 如纪念性建筑、博物馆、档案等。其回忆的认知风格是有意识的心智活动, 如计划性与目的性, 基本属于“冷回忆”。
在阿斯曼看来, 文化记忆的内容主要是宗教、艺术和历史。 (6) 这基本是事实。但我认为, 在文化记忆中, 艺术、历史、宗教并非以独立的知识形态被记住和传承的。在记忆主体那里, 它们是以集体共享知识的形式编码为一个共同体关于“文化自我” (1) 的故事。文化记忆的主题既非“个体生活史”, 亦非“一般社会史”, 而是“文化神话史”。这里的“文化神话”既不同于宗教学意义上的“神话”亦不同于罗兰·巴特的“文化神话”, 作为人的“历史意识”的建构物, 它指的是一个集体通过将自己置于具有时间尝试的境遇, 并借助回忆与想象建构起来的共享假设, 以解释自己的起源。 (2) 如此, 我觉得可把“文化记忆”解释为:某一共同体通过历史信息与文化想象的缀连所创造的“被记住的‘过去’”。这些“过去”不仅超越自传体记忆的范畴, 而且“超越生活之大”、超越社会范畴之上。文化记忆的“过去”, 包括有据可查的信使, 但它并不等于历史。 (3) “这种记忆可以延伸到所称的过去但不一定会延伸到过去的事件”, (4) 它仅仅是“被记忆的过去”。至于这些“过去”中是否真正出现过摩西、黄帝这样的英雄人物, 发生过犹太人与耶和华盟约或庖牺氏始画八卦以及先祖“辉煌创业”的事件, 存在过荷马所描述的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犹太人被掳这样的“苦难时代”、周朝这样的“礼乐时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神话历史化”———“神与超人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 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 (5) ———的编码与“历史神话化”的建构, 通过特殊的文化语言 (6) 、特定的文化形式、特别的文化情境的展演, 使得这些“往昔”不仅仅是远逝“过去”的呈现, 而且能够被相信, 成为传统、权威和宗教, 成为一个共同体文化自我定义的框架、文化尊严的声明、幸福想象的文化神话, 从而使之“遵循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之轨迹生活”。 (7) 总之, 文化记忆所“记忆”的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文化神话。亦因此, 文化记忆的时间结构不限于阿斯曼所说的“神话性上古时代”, 而是一个群体所创造的由古至今“星光缀连”的过去;其主要载体是集体仪式、有形的纪念地、博物馆以及文字、文本系统。在回忆风格上, 文化记忆的唤回不仅完全是意识性的, (8) 还如米尔顿·辛格所说, 是计划性的, 从主题、场景到过程、规则以及引领者都经过精心筹划, 并且充满情感———不仅是怀旧的怅惘, 还有自豪、荣耀或忧郁等所谓“文化乡愁”的那种情感。
虽然我不认同阿斯曼对“文化记忆”内涵的界定, 但对他关于文化记忆中的“神圣”形象即宗教性特征还是认可的。由于文化记忆是对“历史岁月中的‘光芒’”、“往昔生活中的‘黄金时代’” (或“苦难时代”) 、“共同体 (民族与家族) 记忆中的‘英雄圣贤’” (9) 这类集体共享“过去”的记忆, 是对那个超越“凡俗之上”以及日常世界背后神圣“秩序框架”这类非凡的文化意象的呈现, 特别是这种记忆的宗旨是传承世代相沿的集体知识, 为共同体提供连续性的“历史意识”, 因此, 它的叙事路线必须远离平庸的日常世界的形态, 而采取“神圣的”、“权威化”或“圣徒化”的方式来进行, 以免“受来自可选择的历史路线的挑战”。 (1) 而能承担这种“超凡”使命的, 恐怕惟宗教这种文化形态最为合适。其实, 仔细辨析前文我关于文化记忆的界说可见, 它原本就具有宗教的意象, 因而也适合以宗教这一文化机制来承载和呈现。在人类记忆文化史上, 不仅远古时代, 即使在近代乃至于现代世界, 很多共同体都是借助宗教这一特殊文化机制承载、唤回和巩固文化记忆的, 尽管不同民族所选择的“神圣”表达的方式相异。
二、民间信仰:中国文化记忆承载的主体
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是与宗教这一文化形态高度关联的:不仅它的记忆形象而且记忆的载体都具有鲜明的宗教性。虽然中外一些思想家认为, 中国人是一个宗教观念淡漠的民族, 但我想这是他们没有搞清楚宗教并非就是“一神论”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 任何一个集体都需要一个“超凡的过去”这种文化假设表明、校检、巩固其文化身份, 因此, 也需要通过“超凡”文化形态生产和传承文化记忆。不过, 中国文化记忆承载的宗教格式确与以色列、印度等民族的情形不同, 即它不是以神创宗教这种文化形态而是通过浸淫于普罗大众民俗生活中的民间信仰这一形态实现的。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记忆承载的一块重要基石。
人们也许不会认同我的观点。为什么是民间信仰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健全而庞大的文官系统?为什么是民俗宗教而不是中国本土的道教?为什么是民间文化而不是精英化的儒家文化?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民俗宗教, 它所唤起的回忆、所承载的记忆是否可以代表中国民众文化记忆的核心信息?其实, 不止是针对本文的观点, 多少年来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一直都将后者认定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以及文化记忆承载的主体。至于民间信仰, 它不过是“小传统”、“俗文化”, 它所传承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残片, 类似于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半文化”, 既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主流, 更不会成为中国文化记忆承载的主体。我认为, 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中国文化记忆之关系的根本误识。下面就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 中国古代文官系统及其所创造的历史文本确实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记忆提供了可能的传承媒体, 这已然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想辨析的是, 具备某种媒介和使用某种媒介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忆文化。事实上, 中国古代文官系统所创造的文化记忆传承机制, 无论是文字、图像还是身体 (文官群体) , 它们基本上属于高级文化, 大都流动于那些慎独于荒斋老屋的夫子学究的心智系统, 循环于文庙学堂之中, 而对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农耕社会之主体的文化记忆, 无论是家族记忆、社区记忆还是民族记忆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民间信仰这一民俗文化那样明显。我更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文官文化视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士阶层文化记忆的数据生产及存储装置。尽管按照文化记忆理论的另一名家阿莱达·阿斯曼的观点, 文化记忆的存储器作为一种物质的数据载体, 它们是记忆的支撑物, (2) 但文化记忆存储与文化记忆唤回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记忆文化:前者是数据的积累, 后者是数据的提取、表象与再生产;前者仅需要“超身体化”的文字、图像形式即可, 后者则需要“身体化”并借助一定的文化情境 (如文化意象) 、文化形式等多种文化元素才能完成。这也是文化记忆与社会记忆、自传体记忆的根本区别。虽然没有知识生产回忆便无从谈起, 但存储如果不被激活、调取、循环, 它仅仅是“过去”在神经元中的盘存并难免遗忘的命运, 当然也就无所谓文化记忆的循环、传递、巩固与再生产。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体制, 社会顶端的精英文化与社会底座的大众文化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分化, 无论其文化生产还是文化传递都很难激活并重组大众的文化回忆。如果说, 一个共同体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巩固需要集体性、公共性、计划性的循环展演这样一种过程的话, 那么,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中国古代的文官系统只是创造了一种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无人栖居”的历史竹简, 且多浮于社会屋顶;倒是民间信仰通过集体性、公共性的祭祀礼仪、节日庆典等循环的文化展演, 使这些竹简变成了“有人栖居” (1) 的文化记忆, 将“美好的遥远”转换为认同、“计划和希冀”;并且, 这种周期性、模式性的文化展演由于不断激活共同体文化记忆的神经网络, 在此基础上可建构起心智系统中稳固的文化记忆网络连接模式, 从而为调取、保持和传承文化记忆奠定了物质 (大脑灰质) 基础。
第二, 道教虽系中国本土宗教, 但它不可能担承中国文化记忆传承的使命。如果说文化记忆通过“神话历史化”的记忆与“历史神话化”的回忆, 使一个社会群体保持着“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的共享知识和想象活力, 从而校检共同体的认同感、确定集体的尊严感和创造人们的幸福感, 那么, 道教的文化语义、文化想象以及所形成的文化神话实难接合中国民众所需记忆的文化形象、所应唤起的文化想象、所要确认的文化认同, 二者之间撕裂开一个很大的文化裂缝。首先, 道教虽然构建了关于个体身份归属方面的知识, 但其身份归属叙事则被虚无缥缈的神仙故事情节所填充。与以色列通过犹太教、通过《旧约·申命记》所唤起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灾难回忆、历史结局想象以及以色列民族每一成员的神圣责任感不同, 这是一种典型的遁世主义, 是在逍遥解脱、真人仙人的语境下构建的人生意义图谱。“瑶池仙阁”梦幻与华夏民族故土家园、天下大同的梦象属于截然不同的心灵表象。其次, 道教的神职人员与犹太教的祭司不同, 他们的使命不是传承民族的文化记忆, 而是隐遁于山林炼丹修道, 成为仙人、真人, 这使得他们与社会完全脱节开来。至于那些游走于民间的道士, 虽常主持村社仪式, 但这些仪式的宗旨是镇妖捉鬼, 而非文化记忆的传承。
第三, 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记忆之关系, 问题显得复杂一些。我的观点是, 尽管儒家文化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精神习性乃至于集体文化无意识中一直没有断裂的思想体系, 并且也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中国人文化记忆的主题词基本就是儒家的人文主义理想, 但我还是认为, 中国文化记忆的重要承载者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民间信仰。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人们, 我们最好不要把一个共同体“可以回忆的文化”与“可能回忆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事象相互混淆。“可以回忆的文化”在于这种文化叙事的句法结构与故事情节与民族文化梦想乃至于心理深层的文化无意识气脉相通, 构成了文化记忆之“被记住的过去”;但“可能回忆的文化”则在于这种文化系统具有进行文化回忆的动力。或者可以这样说, 在华夏“文化共同体”机体中, 儒家文化如同血液, 民间信仰如同血管, 正是通过民间信仰这根血管, 儒家文化才在华夏民族的机体内流通循环。我不妨稍细一点线条疏解这个问题。
首先, 从文化记忆伦理学这一层面看, 中国传统社会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文化, 但儒家文化并没有形成传承中国社会文化记忆的义务与责任意识。庞大的民间社会仅是一种“半文化”社会, 它需要社会中“秀异分子”的教化与引导, 使得“大传统”在“小传统”中落地生根。然而, 在传统社会, 儒家群体作为社会“秀异分子”并没有自觉文化记忆传承的使命意识。醇儒的使命意识是于庙堂古斋进行精英文化生产;儒生的筑梦蓝图是由儒而仕———“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或至少成为民间社会持有特异生活格调的阶层。 (1) 他们是韦白林所说的“逸豫阶级”。与儒家群体相比, 民间信仰的文化记忆及传承的伦理意识倒是更明晰也更强烈一些。我并不是说民俗文化比儒家文化更具伦理理性, 我只是从民俗心理学这一角度肯定这一点。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下层社会文化, 它不仅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社会学方面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差异, 也意识到在文化政治学方面与上层社会的分化与张力:它是粗俗的因而也是边缘化的。作为一种亚文化, 民俗文化需要吸收上层文化的养分丰富自己, 但也要防止被其同化、排挤掉。正是这种民俗文化心理使得民间信仰建构起文化记忆传承的责任意识:它们需要一种连续性的集体知识以此来进行自我身份定义、文化风格标榜与集体认同的生产。尽管这种文化记忆传承的伦理意识具有文化政治学色彩, 但它毕竟扛起了中国文化记忆传承的重任。
其次, 从文化记忆传承机能的角度审视,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可谓一种周期性乱治交替的历史。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王朝更替如山水轮转。这不仅导致国家层面文化记忆传承机制的碎裂, 也使得那些由儒而吏、由儒而贵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难以维持千年不变的身份与传道文化, 尤其是一些朝代推行的排儒政治, 使得儒家群体传承中国文化记忆的能力基本丧失。倒是社会下层的民间信仰, 通过集体性、循环性、民俗性的仪式, 特别是通过“天地君亲师”的文化神话把儒家意识形态转化为“集体无意识”, 使得文化叙事独立于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 获得了文化表达的正当性, 保证了共同体文化记忆的连续性。
再次, 从文化记忆传承的知识品质这个视阈分析, 如果说, 共同体文化记忆的主要形象是文化神话, 那么, 我们仍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民间信仰实乃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承载的主体。“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的圣贤刚毅, “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英雄气节, 忠义仁爱、孝慈端正的传统美德, “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等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主要情节, 都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话句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转述。人们会说, 这不正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么?它们确系儒家文化的核心, 但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故事原型虽源于儒家却并非儒家输入大众的记忆网络。检视人类文化传承史我们看到, 一个民族在千百年来生存实践中创造出了诸多文化成果, 但大部分都随着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流失了, 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流传。能够记忆下来的文化不仅在于其信息与该民族的“新哺乳动物脑”的神经计算相匹配, 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文化信息与该族群的“古哺乳动物脑”的神经反应相匹配, 即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相通达, 具有“克里斯玛”的性质。如此, 它们才能被敬仰、被尊奉、被记忆、被传递, 甚至可能以荣格所说的“文化原型”的形式实现基因水平的代际传递。总之, “历史神话化”与“文化宗教化”是一种文化传统能否被记忆、被传承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千万年来人类所创造的大部分文化都湮没于历史的废墟之中而唯有宗教文化保存下来的原因所在。儒家文化恰恰缺失这一品质。它如同道、法、墨、兵等诸子百家思想一样, 仅是一家之言而非“圣言”, 因而对它的记忆也就缺失“绝对命令”这一超验伦理基础。恰恰是中国民间信仰这一文化系统通过“天地君亲师”的文化神话和“神祖鬼运巫”的神话文化将儒家的思想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系统, 并以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进行传承。 (2) 几年前我曾指认过这一点:以敬天祭祖和圣贤崇拜为主要文化意象、以禳灾求利和平安幸福为基本文化理想的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传统是相通的。 (1)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民间信仰记忆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
三、民间信仰:文化记忆承载的媒体
文化记忆主题与意义的特殊性, 使得它往往需要特殊的承载媒体。按照阿斯曼的观点, 文化记忆的媒体主要包括文字、仪式以及各种文化机构;阿莱达·阿斯曼将身体与图像纳入记忆媒介系统。媒体形态不同, 传承的效度也不同。犹太人通过逾越节家宴———表演歌曲、故事叙述以及咀嚼苦味的植物和粗糙的食物———的仪式对共同体在法老时代的苦难以及先祖建造城镇的历史进行回忆;基督教以圣餐———分食面包和葡萄酒的仪式对耶稣为了拯救世界而献出生命的圣事进行回忆。这种身体化、感觉化、情感化的媒介都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可产生持久的记忆, 比起单纯的文本知觉在心理系统烙下的印记更深刻, 也更益于集体共享知识的保存与再生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中国民间信仰成了中国文化记忆的承载者, 因为它拥有文化记忆传承的理想化媒体, 即它的表演仪式、文化语言和身体文字。
1. 庆典仪式
仪式是中国民间信仰观念表达以及记忆传承的主要媒介。尽管在各宗教文化系统中, 仪式的重要性都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但对于缺失“圣典”和职业化僧侣团体的中国民间信仰来说, 信仰的巩固和记忆的传承更仰仗仪式这一媒体。对中国民间信仰而言, 仪式就是圣殿圣典、圣像圣物。从仪式与文化记忆传承之关系审视, 社会、族群、家庭记忆, 既以仪式为主要激活器, 亦以仪式为记忆的重要承载体。没有仪式, 神、祖、鬼、巫不过是个体神经网络中漂浮的意象, 宗庙圣地不过是历史河床沉淀的残渣, 甚至于寥寥文本 (如宝卷、宗谱) 离开集体仪式的诵读也仅仅是沉默的文字仓库。正是仪式这种“典礼性社会交往”, 把人们大脑中的神话想象、大自然的地理空间、民间工匠的艺技以及沉默的文字变成了“定型性文本”, 从而使那些自我定义和巩固认同的知识得到巩固和再生产。
作为一种宗教行为, 民间信仰仪式与神创宗教的表现形式不同。如果说神创宗教注重的是通过仪式达到“与神沟通”的奥秘体验, 那么, 民间信仰更注重仪式的社区或族群“文化表演” (米尔顿·辛格, 1972) 的效果。民间社会的“文化”就“封装”在这些表演中。作为一种文化表演, 情境性、展演性构成了民间信仰仪式的个性化风格。情境性即民间信仰仪式总是在具体的地理情境中展开, 如庙宇、祠堂、社区广场等。这种情境性的文化表演于文化记忆之意义如西摩尼德斯的“蜡板和写在蜡板上的字”, 更容易稳固人们关于某些“过去”的记忆;并且, 由于拥有具体的地理情境作为语境背景, 也使得人们的认知域更宽阔, 存储的记忆形象也更丰富、更鲜活 (2) 。
民间信仰仪式的展演具有两个特殊的维度:一是它的定型化;二是它的艺术化。定型化即每次仪式都遵循既定的规范并以重复的方式展开。如果说规范令人严肃、庄重、虔敬, 从而产生印象深刻的记忆, 那么重复则是对这些文化传统之记忆的巩固———以加大输入刺激的方式强化记忆并实现知识的再生产。艺术化即它赋予媒体与表达以审美的属性。理查德·鲍曼通过表演民族志研究向我们展示, 文化表演中的媒体通常都会实现由日常符号系统到表演符号系统的框架性转换, 由于它们代表着文化的风格、关注焦点和兴趣, 使得这些表达性元素组织成了审美的结构, 令人获得经验的升华。 (1) 鲍曼的表述虽显老套, 但他的观点是对的。于文化记忆传承而言, 艺术性媒体不同于日常性媒体, 它不仅通过不同形态的感觉信号, 如视觉、听觉、味觉的输入刺激主体的多感官知觉, 既能激活具体而又活脱的回忆, 又能使人产生审美体验等情感的升华, 从而使得这些知觉不仅以信息摹本的形态存储于意识空间, 还可以情绪、感觉甚至于跨模态知觉等不同形态存储于大脑皮层乃至于皮层下边缘系统, 极易被其他记忆所提取, 产生循环性回忆。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地区每年农历九月廿六—廿八都在双溪江舜王庙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仪式。无论是仪式祭品———“五牲福礼”、三茶三酒三饭———还是三拜九叩之祭礼;无论是绍剧团表演的福禄寿“三星请寿”还是“世代犯人”展演的“忏悔还愿”戏剧, 都创造出一种“文化美学”的展演效果。不同于康德知性美学的“逻辑触觉”, 不同于海德格尔“诗性美学”的神秘返源, 更不同于神学美学的“超验”体验, (2) 文化美学具有一种民俗生活的韵味, 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广场狂欢”。不仅它所展演的文化形象为社区所耳熟能详、喜闻乐见, 而且它的表现风格也鲜活自由、直白朴实、风趣俗气, 给人以喜庆、欢愉的审美体验。由于这种民俗文化知觉、文化美学体验与人们参加民间信仰仪式的世俗化期望, 如观看文化表演、体验传统美好、享受盛宴美味的自然接合, 不仅使人对仪式所表达的内容的记忆具有生态学效度, (3) 而且由于它激活了人们愉快的情绪, 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心情愉快时容易提取这些记忆。 (4)
2. 文化语言
几乎所有关于文化记忆的理论都离不开语言意义的诠释, 语言被认为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体。如此看来, 这里再来讨论语言与文化记忆之关系未免显得太缺乏慧根。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尽管语言作为记忆媒介的价值已为各记忆理论名家所及, 但综观其思维触角和理论视域, 主要还都聚焦于语言的语义层面, 即语言对事件的命名、记录、表现对语义记忆的支撑:在扬·阿斯曼那里, 语言所具有的象征义使得一个群体的文化认同得以构建和传承; (5) 在阿莱达·阿斯曼这里, 语言对事件的命名帮助我们唤回物体和事件而成为记忆最有力的稳定剂; (6) 对哈瓦布赫而言, 正是语言的意义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基本框架; (7) 对康纳顿而言, 仪式语言独特的修辞表达巩固了社会记忆。 (8) 这就是记忆理论触角所探访的语言记忆媒介之功能场。确实, 从认知语言学的原理看, 无论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还是自传体记忆、文化记忆, 它们不仅存储在物件、仪式这些意象之中, 更主要的栖居在语言中。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的重要介质, 而且也是收留世界万物、存储与传递人类文化的基本载体。海德格尔肯定地说:“只要有语言的地方才有人的世界”。 (9) 但我认为, 人的世界的语言筑基不仅表现为早期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所知觉到的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之区域” (10) 、体现于阿斯曼们所说的通过存储、调取而把世界唤回, 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因语言而成为人———因为语言人才有了自我与社会, 才成为文化的动物, 才克服了肉身的先天缺陷而成为这颗小行星上的万物之灵长;在于通过语言———不仅是语义框架、修辞叙事、象征符号, 还包括是民俗经验、历史韵味的展演性言说, 宇宙万物、世间万象不再是人的知觉之流, 而是成为“我的世界”;在于后期海德格尔在“语言之途中”感悟到的通过语言而“成道”。 (1)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语言作为人类文化记忆重要媒体的价值。
为了充分显现文化语言独特的文化记忆媒体功能, 我觉得,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 我们最好对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形式做一区别。今天再用“语言VS言语”的形而上学对立模型来描述这种区别未免显得太俗套, 我更喜欢用梅洛-庞蒂创造的“被言说的语言”和“能言说的语言” (2) 这两个词来区别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形式。前者指涉的是通过人类自然语言系统的词汇和句法以摹本的形式记录、储存记忆, 后者则指人们通过向语言系统植入文化格调、精神习性所激活的情感与想象所呈现和创造丰富的文化记忆;前者可称之为“人类的语言”, 后者可称之为“文化的语言”。民间信仰之所以成为文化记忆的最佳承载, 就在于它操演着文化记忆的“文化语言”。尤其是民间信仰的仪式言语, 它与“被言说的语言”不同, 形成了具有浓郁社区与族群文化经验的修辞构式和言说体式:不仅是庄严肃穆的文风、定型的语汇系统与修辞组织, 而且作为“言说民族志”所说的“文化特殊性的范畴和功能” (3) 之叙事系统, 涌现出鲜明的民俗个性, 即它不仅通过特殊的句法形式显现着一个家庭、社区或共同体古老的言语习俗, 而且它的民俗化、生活化、情感化叙事所激起的复杂的感受质体验, (4) 也使人们不仅看到了社区的过去, 还仿佛闻到了亲人的味道, 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倾听到了蜷曲在言辞中的神鬼的呢喃, 成为对“沉睡的过去”最有力的招魂。比如, 民间信仰仪式上, 无论是神话讲述、戏剧表演还是祈请礼拜, 都是以民族、社区的言语习俗、地方经验、民俗信仰等文化感觉构造句法和叙事的:绍兴会稽山地区的舜王祭祀仪式操作的是吴方言与越剧语言;闽南的妈祖祭祀礼仪使用的是闽南话与南音符号;中国北方不同民族的萨满教仪式使用的是满族、蒙古族、赫哲族等民俗言语。这些散发着牛羊、草原、汗水、泥土味道的“文化语言”不仅产生了最佳的通达性, 即使参与者产生最强烈的亲熟感, 而且因其具有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所说的“历史感”及其所产生的“深描”性, (5) 也激活了人们的情绪与想象, 使存储的记忆也更持久。 (6)
总之, “能言说的语言”之于文化记忆,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记忆提供路标和框架, 还在于它所激活的记忆活力和灵性。一个方言词汇、一句本地谚语或一则本土传说, 不仅把一个消逝的世界还有其中的某个情境带了回来, 而且也激活了大脑的知觉网络, 将“记忆屏幕”上那些模模糊糊的“过去”意象编辑成一个清晰而丰满的文化神话界面。因为我们表征了房屋, 所以也能表征出家庭、祖先以及往昔岁月。
3. 身体文字
从“身体考古学”的视角看, 人类的身体不仅是生命的基石, 也是灵魂的驻地, 是人类文化经验存储与流转的活的媒介。它不仅通过烙印其上的某些历史印记和修辞 (7) 方式, 而且也通过将分化于其物理、化学成分之中的知觉、经验的言语化实现了生命体验由私人领域 (意识) 到公共领域 (语言) 的脱胎换骨, 传递并创造着鲜活的个人、社会、文化记忆。尤其是在口述传统中, 人类的记忆, 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 主要是通过身体文字进行传递的。身体就是一张画满了各种符号的羊皮纸, 通过那些或深或浅或动或静踪迹的阅读, 不仅可唤醒记忆而且还使得回忆“血肉丰满”。身体语言的文化记忆媒介功能, 在中国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形态中尤为凸显。民间信仰组织的长老、香头、北方民族的萨满以及社区、家族的老者, 都可谓以身体为媒介保存和传递集体文化的。
首先, 让我们来关注“血肉生态”场中的叙事。在家庭祭祀仪式或家族聚会上, 族长、主祭大萨满等老者常常通过自己的身体之“灵” (言语) 追忆自己、家庭、家族以及社区的往昔。按照老年心理学理论, 老人的往事追忆基本系出于逃避、强迫以及“第一次经历”的深刻印象、定义和说明自己的身份等心理需求, (1) 但这不完全是事实。哈布瓦赫曾这样解释老年人的忆旧心理:“老年人阅历丰富, 而且拥有许多的记忆, 既然如此, 老年人怎么能不会热切地关注过去, 关注他们充当捍卫者的这一共同财富呢?正是这种功能给了他们现在有权得到的惟一声望, 他们怎么能不会刻意地努力履行这一功能呢?” (2) 我认为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 那些外向性高、责任心强的老年人, 主要是企望通过这种忆旧性叙事把集体和个人的文化进行确证和再生产并传递下去。我相信, 人作为语言动物之伟大性, 不仅在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因语言而拥有自我和世界、历史与传统, 更主要的还在于人意识到他是“类”世界的一个中介, 他的肉体仅仅是人类历史文化川流中的一个涵洞。人此在的使命就是通过自己身体这一“符号作坊”不停地“编织文化动物的生命线”。民间社会老者的忆旧绝非源于记忆心理学之本能和记忆社会学之动力, 而是记忆伦理学之动力。作为上层社会和主流文化之边缘的民间社会和民俗文化, 只有保证集体“过去”的连续性传递, 才能保证集体历史意识的连续性。也正是这种记忆伦理, 使得在民间社会的某些老者成为族群文化记忆的守灵人, 如长老、祭司、萨满等。特别是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社会的宗教文化不同, 由于“圣典”的缺席以及专业性的僧侣团体和职业人 (如荷马式的歌者) 的缺失, 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主要靠口述传统, 其传承和巩固之责便落于族中的长者、民间信仰组织的长老和祭司、萨满的身上。例如, 在满族家祭仪式上, 老萨满都会讲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本族 (本支) 发祥、自然变幻、灵魂神气以及氏族萨满、祖先成为英雄神灵的神话传说, 以娱人乐神, 崇德极远。故萨满也被族人视为思想开化、文化传承的“蒙师与先导”。 (3) 在汉民族中, 社区或宗族的长者、族长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组织的首领则成为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传递者。尽管按照神经生物学理论, 人类大脑的生物属性使得记忆的本质乃是遗忘, 尤其是人至老年, 分子生物系统的退化, 更可能导致老年人心智系统存储的信息丢失。但这一规律仅限于社会统计学和普通老年心理学范畴, 对于民间信仰的长老以及族群、家庭的长者而言, 这一记忆的认知规律并不适用。人至老年, “朝花夕拾”的忆旧是老年心理生活的主要模式, 特别是某些老人在忆旧的叙事加工和自传推理中不仅体验到了通过这种活动激活文化自我图式、延续文化传统这样一种存在价值, 而且也体验到了逃避孤独、排解烦倦、降低抑郁、提升自尊、自我实现的幸福感, (4) 这使得他们更喜欢忆旧, 因而也就避免了记忆的生物机能退化与存储信息的丢失。而且, 毋容置疑, 老年人的这种“忆旧”生活习性还可能通过环境作用建构后代的“社会基因”, 使得这一记忆传递的习俗代代相传。
我之所以将老者在集体空间的忆旧叙事解释为一种“肉体文字”而非普通的文化语言, 不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场域———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不同, 更重要的在于这一叙事语言超越了人类自然语言的属性, 即在文化语境———历史的证人、神性的人格 (如萨满) ———和“生态语境”———讲述者苍苍的白发、苍老的面孔、神秘的面具、远古的喉音 (如满族祭祖仪式上萨满的“鄂罗三声” (1) ) ———的共同作用下, 由身体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集体共享的不可怀疑的“历史记忆”。“在我爷爷的年代……”、“头辈太爷……从始至终/住长白山/在三个山峰之上/从三道河到松花江……由大瀑布下来……” (2) 人们不仅通过这些古朴悠远的声音“追忆和再现先人遥远的星光古洞生活”, (3) 而且还通过将这些声音与语境的联网创造着“遥远的星光古洞生活”, 跟随声音走进那个空旷悠远但却“有血有肉”的非凡“往昔”。 (4) 显然, 由这些“肉体语言”知觉所烙印的记忆的心灵深度是文本阅读、档案查阅以及图像观看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其次, 我们再来透视另一种肉体文字———疤痕的文化记忆媒介功能。作为往事的书写, 肉体疤痕, 无论是纹身还是创伤, 都不仅仅是身体事件, 而是一种心灵事件和文化事件。在人类记忆文化史上, 肉体一直被视为羊皮纸, 疤痕就是书写其上的文字;或者说, 疤痕就是用图案书写的往事, 用血肉筑就的纪念碑, 远逝的“过去”就寂静地蜷伏在这些凸凹不平的肌理中。“这是和邪恶的精怪斗法时落下的伤疤……”这些肉体疤痕所唤起的伦理主义、英雄气节或苦难的“形象”回忆在或自豪或忧郁或痛苦的语调的衬托下, 使得“家庭共同邂逅自己作为家庭而拥有的历史……是在给家庭成员对自己家庭的社会认同的坚信礼。” (5) 它们不仅在视听者的心灵烙下鲜活的记忆, 而且, 这些知觉信号也会激活人们的情感, 使得输入的存储更牢固。 (6)
四、民间信仰:文化回忆的积极过程
若欲使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保持鲜活与恒久的生命力, 不仅需要得力的媒体承载, 更需要活力性的回忆过程。根据记忆心理学的原理, 文化回忆过程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过程”指的是有益于激活、唤醒、建构、强化文化记忆的情境和行为, 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事件、人物和地点的具体形式” (7) 组成的时空框架、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能“让时间停止……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不变、让死者不朽”的“化身变形能力”的记忆场; (8) “消极过程”指的是那些易导致记忆的碎片化、零散化、健忘化的情境和行为。与概念和命题即语义表征不同, 意象由于其情境性 (如具体的场景) 和形象性 (如人神意象) , 使得它成为欧洲16世纪记忆术大师卡米罗所说的“记忆剧场”, 那里存放着“事物、语言”等。 (9) 知觉不仅更具细节性, 且常常携带着情感。以心理意象和情感体验风格形成的知识表征, 使得对表征的“真理”具有“鲜明、生动、深刻、情境性等特点”。 (1) 基于文化回忆过程的这一原理, 我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属于文化记忆的“积极过程”。民间信仰文化回忆的“积极”特征, 一方面表现于其信仰的“真理”通常都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另一方面其回忆过程亦围绕着具体的情境而展开。这些情境, 既是唤起文化记忆的活力机制, 又是强化文化记忆的认知元素。
我们先来分析民间信仰的“真理”及其回忆的时空情境特征。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说, 人类记忆的基本信息都是关于世界知觉经验即时空经验的存储与编码。哲学家C·麦金曾说:“世界的空间性是某种我们无法躲避的东西;它事实上烙印在我们所有经验中。……空间知觉是人类 (和动物) 意识本质的一部分。” (2) 不仅空间, 时间也同样是人类知觉经验或者说意识的重要构架。空间给动物以生存的方位感, 而时间则给动物以生命的节奏感。空间感与时间感甚至刻入了动物的基因之中。作为人类知觉经验存储的记忆, 基本都以具体的时-空为框架进行存储和调取。尤其是作为共同体共享假设的文化记忆, 因其内容大都超越了“当下与日常”, 因而更需要根植于具体的时空意象之中。文化神话只有附体于具体的时空意象之上, 才便于以“历史”的姿态呈现给人们, 并使得这种“历史”被确证。
宗教史学家伊利亚德告诉我们, 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根本区别, 就在于宗教文化总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将时间与空间神圣化, 从而赋予世界与生命以“非凡”的意义。这基本符合事实。作为一种非共时事件的宗教, 它必须通过某一空间与时间的超凡化被引入到现实领域并使现实神圣化。这一“神圣”生产的原理, 同样适合中国民间信仰。首先, 民间信仰大都按自然节律形成相应的节日庆典。从民俗发生学的视角观察, 最早出现的节日是岁时节日。它的发明初衷并非为了创构一个与日常时间相对的非凡时间, 而是为了对时间之流进行切割标段, 从而使得绵延、混沌的时间之流节奏化、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结构化。但是, 随着节日的循环和文化想象的扩张, 神话、传说、运理等植入节日并再对节日的内涵进行再生产, 此时, 节日就不再仅仅是时间节奏的符号, 而是成为“日常的”和“神圣的”存在的划分, 成为人们与神灵、祖先等非共时存在相遇的时间, 如汉民族民间信仰中的社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下元节、祭灶日、春节以及各种神灵、英雄、圣贤诞辰日等。它们与日常时间划出了一个清晰的时间界域:在这些时刻, 神 (自然神、英雄神等) 、祖、鬼等这些非共时存在被引入共时域, 或者说日常生活中这些缺席的不在场者被召唤在场。非共时者的共时化, 不仅是在日常时间之流中切分出一个超凡的时段, 也不单纯是为使得日常世界发生某种“震撼”, 其重要意义在于这一“梦幻时间”不仅奠定了“可唤醒的过去”, 而且也联结着“未来与希冀”:通过节日庆典、通过以具象的形式模拟当时的情景和境遇以及重新“体验”过去的时光, 使得那些在日常世界中遭到压抑、边缘化或已缺席了的“过去”记忆再次被唤醒、被召回、被建构, 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黄金时代”、“英雄创举”、“开山立业”之宏伟图像重新浮上精神的地平线, 并通过往昔的超凡之光映射当下, 日常世界“瞬间闪耀/它们被神圣的光焰点燃”。 (3) 于是, 节日不再仅是某些时间的重复, 而是变成了人类体验“双重时间”的生命戏剧。特别是民间信仰节日庆典的宏大性、展演性, 不仅使得这种回忆以阿比·瓦尔堡所说的“集体图像记忆” (4) 的形式而展开, 而且由于展演的美学意象, 激活了人们的情感, 使得这种回忆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 “即便神话的历史是虚假的, 它至少以纯粹的和更具标志的形式同样表现了某一历史事件的特征”, “逻辑偶然性和情绪波动双重性的非理性嵌入合理性之中”, (1) 使得记忆更具“历史”感。
其次, 民间信仰也通过具体的空间意象积极唤回人们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民俗宗教, 中国民间信仰基本由三种文化系统构成:观念、仪式、象征。信仰系统主要包括神灵、祖先、鬼、运、巫;仪式系统包括各种祭祀、庆典以及巫术活动;象征系统则包括神系、自然物、地理情境等。这三种系统大都被安置于符号化的空间 (包括将某些空间转换成可触可及的地点) 结构之中。如神灵信仰, 无论是天神、地神等自然神还是圣贤神、英雄神, 大都联结着具体的地理空间背景, 尽管有的空间显得比较空虚;祖先信仰则与可感知的地点融为一体, 即家;对鬼的信仰也往往具有地理空间性, 如城隍庙、东岳庙等。由于其信仰的“真理”空间化了, 故表达这些信仰的仪式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空间-地理框架而展开:大多数神灵祭祀以社区为主体, 地理空间以庙宇为中心;祖先祭拜以家庭为中心, 地理空间在祠堂, 满族在家宅的西炕以及西南方向的古树下或岩石上、泉源头;鬼灵祭拜和巫术活动作为人类学家所说的“集体灵魂”运动, “无法在抽象的层次上开花结果”, 必须借助环境提升其奥秘和魔法的效力, 因而它总是发生在十字路口、墓地、社区边界、门槛、灶边等这些具体空间。 (2) 在象征系统中, 某些自然地理由于被附身了某些神话、仙话、鬼话而成为哈布瓦赫所说的“传奇地形”, 即所谓的“圣山”、“圣水”、“圣地”:浙江绍兴地区舜王信仰中的握登山 (上虞) 、会稽山南的“象田”、余姚历山南的石板石块 (石眠床、石马桶、石脚桶、石尿瓶) 等遗迹成为当地民间信仰者心中的圣地圣迹;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山是京郊民间信仰———“四大门”崇信者心中的“圣山”;辽宁闾山系“歪脖老母”崇信者心中的“圣山”;甚至于荒郊野外的老树怪石、废墟洞穴等也都因猫头鹰的静穆哲思、狐狸的孤独徘徊而成为善男信女朝圣与拜谒的地方。
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观念、仪式、象征三种叙事系统的空间特征分析, 我们还可以捕捉到这样一点:中国民间信仰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故事散漫无序、句法繁复多元的文化神话, 而是具有一个视角和情节都比较固定的叙事框架, 这就是家庭这个场所。在一个缺失“神圣”与“世俗”之明晰分别的世界里,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空间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浸透了“神圣”的成分。在观念系统层面, 祖先崇拜自不必说, 即使是神灵崇拜也基本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土地神、灶神、门神、床神就是家神;甚至于鬼魂也隐藏于房前屋后的某一地方。在仪式系统层面, 很多仪式庆典都是以家庭为空间展开的, 如灶神祭、财神祭、亡灵 (家鬼) 祭以及各种人生礼仪。在象征系统层面, 诸多符号亦与家庭密切关联, 如文字系统 (家谱) 。对于中国人而言, “家”不仅仅是一个养育自己的社会学单位, 也不仅仅是一套纵横交织的亲属关系网络, 真正活跃于人们大脑中“家”的表征的是栖居着某些神灵的空间、放置着祖先物件的地方、浸入了某种情感的场所。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言, 我们之所以将房屋视为亲切的家和地方, 并非因为整幢房屋, 而是可以触模和闻到的阁楼和地下室、壁炉和飘窗、隐蔽的角落、凳子和镜子。 (3) 正是通过“家”这一“心理地理”空间意象的浮现, 人们的记忆被一次次唤醒, 回忆的图谱也从家庭延展到集体的“过去”这一广阔的场面。我们不妨以祖先崇拜为个案做一分析。
祖先崇拜的意义一向被学者们解释为“慎终追远”的伦理叙事和祈望庇佑后代的社会认知。我觉得, 这仅仅是中国民众祖先崇拜的心灵维度之一。此外, 这种信仰也是维系家庭记忆, 促进自我概念的保持, 从而形成一个跨时空的、清晰的自我同一感的文化认知方式, 就像荣格在波林根的仿古塔楼里所产生的对列祖列宗生活的回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同一感一样。 (1) 而对“祖先生活”的回忆则以“家”这一空间意象为媒介的。祖先, 对于家庭集体记忆来说, 不是一个远逝的幽魂, 也不是一个与“我”生物性连接的心理图式, 它就是家庭中某一具体的空间———家庙或宗祠以及房屋中的位置, 甚至于放置祖先遗留物的地方。正是这些家庭空间维系着家族的祖先记忆以及集体知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 对家庭“祖先空间”的记忆和由它们所唤起的回忆, 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祖先意象的唤回和对自己集体成员身份的再次确认, 从中国社会“家-国一体”这一视角观照, 祖先与家庭记忆的复活实质是卢卡契心灵中那个“星光照耀”、“天下欢乐”时代的浮现。 (2)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民间信仰文化回忆的实体情境特征。
这里所谓的“实体情境”, 我指的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与人们照面的物件, 包括祖屋、祖先、圣贤、英雄留下的遗物, 如衣服、器具、工艺品等所构成的记忆和回忆意象。家族保存的先人遗物, 无论是祖屋还是那些具体物件, 它们不仅是一种物质实体, 更是一种精神实体。通过赋予这些物件的“历史”以特殊意蕴, 它们由一般“器物”变成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能指符号”, 起着一种“迷人的作用”———“人们可以不断地把意义纳入这种形式中”, (3) 成为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叙事以及集体文化回忆的“图像”。通过在节日里讲述这些物件的“故事”和“瞻仰”这些物件, 知觉所激活的不仅是其作为一种文物的文化经济学意识, 而是“看到祖上使用过的器具, 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温它们过去的使用者的生活”, (4) 并涌动着一种或自豪或感慨的情感。它把人的精神带回到往昔岁月, 并通过“过去”之光照亮当下的自我。
注释
(1) (1)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金寿福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页。
(2) (2) 我指的是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所推动的“怀旧”、“寻根”、“乡愁”之类的话语喧哗。
(1) (1)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第44、46、47页。
(2) (2)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 袁志英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第105-106页。
(3) (3) [美]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感受发生的一切:意识产生中的身体和情绪》, 杨韶钢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07、155、177页。
(4) (4) 以文本形式 (传记) 形成的个人记忆不属于生态性的自传体记忆, 它们是“我想要记住的”而非自然记忆。
(5) (5)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李斌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序”第6页。
(6) (6)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 陈新、彭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 (第一辑)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8页。
(1) (1) 关于“文化自我”的概念内涵, 请参阅高长江:《艺术与人文修养》,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111页。
(2) (2)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傅铿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6页。
(3) (3) 历史只能导致皮埃尔·诺拉所说的对文化记忆的“祛魅”。 (见[法]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95页)
(4) (4)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指认了集体共享记忆传递“神圣化、权威化”路线的这一考量。见[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贺海仁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54页。
(5) (5) 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 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第47页。
(6) (6) “文化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 表现为表述的规则性、定型性和风格的庄严性以及意象的民俗性, 如神话传说、家族故事以及神圣文本。 (参见高长江:《萨满神歌语言认知问题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60-61页)
(7) (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第322页。
(8) (8) 荣格所说的“祖先故事”在后代生命组织中刻下的印记即“文化原型”的无意识表达所形成的心灵表象不属于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内容。
(9) (9) 这里的“英雄圣贤”包括祖先。在中国上古时代, 氏族英雄就是氏族祖先。随着历史的发展, “英雄”与祖先虽分离开来, 但中国人祖先崇拜同样具有“英雄”、“圣贤”崇拜之内涵。不是每一个共同体都需要一个家系和“根”的归属, 而是每一个共同体都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史前史”、一个“超凡的过去”这种文化假设来声明、校检并巩固其文化身份。所以, 中国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族谱, 把自己的祖先和家系与历史上的某个英雄、圣贤联系起来。
(1) (1)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指认了集体共享记忆传递“神圣化、权威化”路线的这一考量。见[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第55页。
(2) (2)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第13页。
(1) (1) 关于“无人栖居”和“有人栖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请参阅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第146页。
(1) (1) 参阅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30-31页。
(2) (2) 我认为,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鬼、运、巫意识, 并非单纯的蒙昧意识、神秘心灵的表征, 它们的背后活跃着人们扬善弃恶、追求和谐的道德想象, 如“善鬼”的敬奉与“恶鬼”的驱逐、“运道”背后的“人道” (伦理道德) 元素等。
(1) (1) 高长江:《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 《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2) (2) 认知心理学家研究表明, 伴有意象的记忆比起单纯的语义记忆更具有细节性, 也更易提取。
(1) (1)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杨利慧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90-91、92页。
(2) (2) [瑞士]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 曹卫东等译, 三联书店2002年版, 第91页。
(3) (3) 认知心理学家指出, 记忆的信心源于生动并细节丰富的环境知觉。 ([美]斯滕伯格:《认知心理学》, 杨炳钧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8页)
(4) (4) 参见[加拿大]齐瓦·孔达:《社会认知》, 周治金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 第124页。
(5) (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第145页。
(6) (6)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第284页。
(7) (7)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毕然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80页。
(8) (8)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69页。
(9) (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在》, 王作虹译, 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第116页。
(10) (10)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第317页。
(1) (1)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229页。
(2) (2)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 杨大春译,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第10页。
(3) (3)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第316页。
(4) (4) 关于语言的复杂的“感受质”体验问题, 请参阅我的新著《萨满神歌语言认知问题研究》, 第287-288页。
(5) (5) [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第33页。
(6) (6) 详见高长江:《萨满神歌语言认知问题研究》, 第161-165页。
(7) (7) 这里的“修辞”不是语言修辞学的含义, 而是指体态变化的技艺。
(1) (1) [荷]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风景》, 张朝霞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第213-214页。
(2) (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第85页。
(3) (3)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00-202页。
(4) (4) 西方心理治疗界和东亚的日本、香港、台湾近年来的老年临床心理治疗——“忆旧叙事治疗”的大量临床数据支持了我的这一观点。
(1) (1) 参见关杰:《神圣的显现——宁古塔满族萨满祭祖仪式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228-229页。
(2) (2) 《吉林九台佛满洲石克忒力氏族祭祀神本》 (东哈本) 。
(3) (3) 王宏刚、富育光:《满族风俗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第136页。
(4) (4) 我在《萨满神歌语言认知问题研究》一书系统讨论了面孔加工对认知行为的影响。请参阅该书第七章。
(5) (5) [德]安格拉·开普勒:《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 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第99-100页。
(6) (6) 尽管随着生命的死亡, 肉体的毁灭, 会影响这些肉体文字的传递效能, 但通过胶片与颜料留下这些痕迹, 便弥补了其的这一短板。
(7) (7)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第329页。神经科学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也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回忆的事件越是与具体的场景相关联, 就越能引发回忆活动中尽可能多的联想, 也就越可以巩固这些记忆。 ([英]苏珊·格林菲尔德:《人脑之谜》, 杨雄里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第121页)
(8) (8) [法]皮耶·诺拉:《记忆所系之处》, 戴丽娟译, 行人文化实验室 (台北) 2012年版, 第一卷, 第27-28页。
(9) (9) [英]弗朗西施·叶芝:《记忆之术》, 钱彦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第137-139页。
(1) (1) 杨治良等:《记忆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416页。
(2) (2) [英]C·麦金:《神秘的火焰:物理世界中有意识的心灵》, 刘明海译, 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91页。
(3) (3) [德]荷尔德林:《如同在节日的日子……》, 《荷尔德林诗集》, 王佐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02页。
(4) (4)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
(1) (1)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李幼蒸译,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276、277页。
(2) (2) [法]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法]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杨渝东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91、59页。
(3) (3)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王志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117页。
(1) (1) [瑞士]古斯塔夫·卡尔·荣格:《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刘国斌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200-201页。
(2) (2) 中国思想家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的社会制度”甚至于政治制度——“君臣关系是家庭父子关系的一种投射。”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9页) “中国人常只知有家而不知有社会”。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 第14页)
(3) (3) [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73页。
(4) (4)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第1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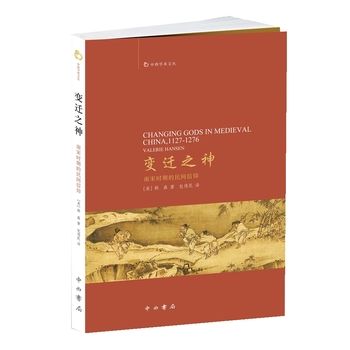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