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重庆]民间信仰中的信息沟通与传播 |
| ——基于对福建莆田民间信仰田野调查的思考 |
| 作者:吴重庆 | 原载《东南学术》 |
摘 要: 在民间信仰中,人鬼神之间的互动,关键在于信息沟通与传播。阴阳分隔导致信息不对称、信息需求与信息沟通。鬼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呈现出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特点。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是作为灵媒的“童乩”与“卜杯”,不同的灵媒,决定了人神互动的不同模式、神明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神明供给的不同信息类型。神明供给的信息可称为神圣信息。神圣信息的传播在特点、机制、规律上都不同于一般社会信息的传播。 作者简介: 吴重庆,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在我国广大乡村丰富多元的民间信仰活动中,主要是围绕着人鬼神之间的互动——鬼作扰人,人敬神、求神,神明为人指点迷津,驱邪解厄。人鬼神之间的互动是乡间信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人所在的社区,鬼、神明也是特殊的社区成员。鬼携带社区的“往时”记忆,神明察古觉今断未来,与“现时”的人互动,过去、现在、未来交融,此所谓“共时态社区”。在此“共时态社区”里,活着的人不仅需要为其现世的行为负责,更需要为其前世以及祖上负责。所以,在信众貌似未开化的日常生活中,其生活空间其实远比受现代性支配的文明人广大悠远。 在人鬼神互动的“共时态社区”里,所谓“互动”,其实不过是凭借“灵媒”(spirit medium)传达神明指点予人、鬼索求予人的信息,人据此采取相应的还愿和避邪行动。人鬼神之间信息的沟通,是民间信仰的核心环节。本文是在对民间信仰发达的福建莆田地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所作的一些较具概念化色彩的思考。 一 阴阳之际的信息需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记梦》 苏轼在词中对亡妻的思念之苦缘于亲人逝后天人永隔、信息阻断。在民间信仰中,人一旦去世,即作别生人所在的阳间而以另外一种生命形式进入阴间。阴阳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与区隔,是不可以随便穿越的,生人与死者不可直接沟通,不然何来“生死之别”?正是阴阳区隔导致生人与死者之间的信息阻断,导致生人与死者之间巨大的信息需求。 在阴阳之际的信息需求中,存在两种类型,即思念型信息需求(如苏轼思念亡妻)与解惑型信息需求。 思念型信息需求是指生者思念在阴间的故人而需要阴阳之际的信息沟通。思念型信息需求不过是为了满足在世亲人一时的情感需求。人去世后,家人为其“做七”,每七天为一个祭日,从“头七”到“尾七”,七个“七”共四十九天。“头七”迎接亲人的亡魂回家,“尾七”则需要准备大量冥币、纸糊的轿子、马匹坐骑乃至现代家电如电视机、手机、洗衣机、煤气灶、沙发、套房、小汽车等供奉给亡魂。待诵经礼忏的仪式结束之后,便将上述纸制祭品焚化。家人思亲心切,一般在“尾七”结束后即试图了解新亡故人在阴间的详情。例如,在民间信仰发达的福建莆田乡村,思念型信息需求的获得是通过一个称为“求八龟”(根据莆田方言发音)的特殊途径。“求八龟”的程序是:求阴间信息者先焚香“呼神”,默念自己所欲了解的内容,然后就在一旁坐等。据说,附体于“童乩”身上的“八龟”派神探“舍人仔”(根据莆田方言发音)到阴间,可以找到任何阴魂。“舍人仔”打探到后马上反馈给“八龟”,“八龟”就会喊“新亡”(新近去世)、“旧亡”(三年前去世),“一朵红花”(指去世的人育有一个女儿)、“两朵白花”(指去世的人育有两个儿子)。在旁等候消息的家属听到“八龟”的喊声就可判断其所指是否为自家的故人。若是,即趋前询问已故亲人在阴间的具体状况。为“八龟”附体的“童乩”往往一边哭一边唱,如果说中了实情(如几岁去世、得了什么病、家里还有什么人等),家属就会跟着痛哭,认定自己故去的亲人此刻就在眼前。家属一般是询问亲人去世时加穿的寿衣以及做“尾七”时焚化的一系列祭品是否得到,有没有被野鬼抢走,现在阴间做什么,是否辛苦,以及墓穴是否温暖,等等。这种阴阳相会的时间是有限的,通常在半小时左右。在亲人的亡魂即将退去之际,家属紧握“童乩”的手不舍,观者无不动容。这阴阳对答过程往往被家属现场录音,回家之后再将此录音播放给其他家庭成员听,以缓解失亲之痛。 解惑型信息需求是指当家庭成员遭遇病灾厄运时需要“请教”神明指点迷津消灾解厄。解惑型信息多用于解燃眉之急和切身之痛,所以,信众在解惑型信息的获取上,往往比思念型信息更舍得付出时间与金钱。由于乡村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程度较低,村民往往没有及时医治疾患,“小病拖大病抗”,结果急性病变成慢性病,局部病变成疑难杂症,再去寻医问药并无明显疗效。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运动之后,一般村民其实是崇尚科学信奉医学的,“药到病除”是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一旦遭遇药到而病不除的情况,自己或者其家人就会怀疑疾患不去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鬼的作扰所致。村民对久病不愈的应对之策是“既要医生也要菩萨(神明)”,即科学的归科学,信仰的归信仰;该寻医问药就寻医问药,该“请教”神明就“请教”神明。在“请教”神明为自己或者家人指点迷津的信众中,久病不愈者占了大多数。另外一种情况是家运不顺,如做生意屡屡亏损、晚辈们在婚育上不如意、车祸、工伤等不幸事件连连。“为什么别人都顺利呢”,这是急于“请教”神明的信众们郁结在胸的问题。一般说来,神明的解惑指点,提供的都是阳世的当事人凭其现世人生经验根本无法获得的信息:如“前缘”,即前世本为夫妻,如今一方在阳世已与别人结为夫妻,而留在阴间的另一方找上门来,要求复婚(所谓“合卺”),故作扰致使对方屡屡患病;如“蒙冤”,即阴间某鬼前世受某家户的祖上冤枉致死,今日终于找到了冤家后裔,故作扰要求该后裔为其祖上补过;如“讨食”,即由于年代久远,某家户忘了祭祀远代先祖(亦称为“顶代公妈”),要求给一口饭吃(亦称为“一嘴食”);如“犯冲”,即某神明巡游路上,小孩或妇人(女性因经血原因,常被视为不洁)盲目不避,神明动怒或被神明的坐骑踢了一脚甚至只是被神驹扬起的尾巴扫到。凡此等等,令信众感慨人生的不测与凶险。所以,对来自神明的解惑型信息的供给,信众一律奉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虔诚态度。再者,对神明的解惑型信息即使心有存疑,也无法凭现世人生经验加以验证。 由上可见,不管是思念型还是解惑型的信息需求,都是由于人鬼神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人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流动。鬼所携带的信息是现世的人所不具备的,即鬼记得与现世人的前世的情感纠葛,记得与现世人的祖上的冤仇;现世人所具有的信息是平面的、当下的,尽管人们深知“冤有头债有主”,但凭借现世的人对信息的平面化掌握,无法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追溯到前世或者祖上。而神明可以跨越阴阳两界的区隔,鬼作扰人的把戏即便再隐秘,也逃不过神明如炬的目光,况且神明还可以为人预判未来,警告人们做好驱邪避害消灾解厄的预案。神明属于超时态存在,其记忆之历久及信息之周全远在鬼之上(后者可能因投胎转世而重新从阳间开始记忆)。可以说,信息的不对称构成了权力的等级。因为神明掌握最为周全的信息,所以在人鬼神关系中成为最有权力的角色。人之畏鬼,是因为人处于茫然无知状态,无从了解前世或者祖上的纠葛,无从为自己的前世及祖上的行为负责,从而也无从规避鬼的作扰。人之敬神求神,请教神明,是为了获得稀缺的信息资源,减少不确定性。信息的获得即不确定性的减少,这对现世的人来说是一项大的收益。严格地说,神明并非能够保证人一生平安发财,神明只是给人提供如何应对鬼的作扰的办法从而防范其对人的福祉的损害。 二 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发明“差序格局”概念,用于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方式及人的行为特征,“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差序格局”中,行事交往注重亲情,讲究亲疏远近有别。“差”可以理解为行动者的情感投入有轻重,其与关系的亲疏成正比,关系越是亲近,行动者的情感投入越重,关系越是疏远,行动者的情感投入越轻,由此构成差等;“序”指行动者的情感投入有缓急,其与关系的亲疏成正比,关系越是亲近,行动者的情感投入越急,关系越是疏远,行动者的情感投入越缓,由此构成次序。陈少明在阐述“差序格局”时认为,行动者的情感投入之所以需要区分出轻重缓急,是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无法一视同仁,不得不讲究差序,“每个个体能力或拥有资源的不充分,也没法支持其全面施爱的行动”,“儒家爱人的社会理想,是兼顾其实践的可能性的”。这种解释偏向于对行动者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是孤立的个体,不是“社会—文化人”,而且行为科学的研究也不支持“理性人”自利的假设,如镜像神经元就被认为是“感同身受”“设身处地”之类道德行为的生理基础。如果我们将行动者假设为“社会—文化人”,那么,行动者的情感投入之所以需要区分出轻重缓急,可能是因为行动者的感同身受——与自己关系越近,就越是能够就近切身感受其苦痛,就越是愿意为其分担付出。所以,“差序格局”中行动者的行为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血缘纽带作连接的体恤与同情。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解释的是中国乡土社会中人的行为特征。如本文开头所述,鬼与神明其实是作为特殊的社区成员与现世的人共处于“共时态社区”。在这个“共时态社区”中,人鬼神之间的互动,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这体现在鬼对人的信息传递上。 人死后如果得享子嗣祭祀供奉,那么这个亡魂是不会被认为鬼的。在信众的眼里,鬼是指那些没有定时收到子嗣祭祀供奉的亡魂,哪怕是自己的祖宗。如下几种情形都导致亡魂无法定时收到子嗣的祭祀供奉:第一,有子嗣而无祭祀供奉。有些祖宗由于代际相隔过于久远(所谓“顶代公妈”),以致子嗣忘记其存在而没有祭祀供奉,或者忘记其生日及忌日而没有定时供奉,那么这些祖上亡魂就会找到子嗣“讨食”,要求或者暗示子嗣定时祭祀供奉。这些前来“讨食”的祖上亡魂,被子嗣们略带轻蔑地称为“公妈鬼”。第二,有子嗣但祭祀供奉不到。如果祖上不是在家中去世,而是在野外非正常死亡或者客死他乡,这种情形被称为“散亡”。在民间的观念里,人死在哪里,其魂就坠在哪里。显然,“散亡”者的魂是回不了家的,只能在野外游荡。即使有子嗣,也无法在家中祭祀供奉。“散亡”的亡魂由于无人祭祀供奉,所以历来被信众视为野鬼、厉鬼。一旦有“散亡”的事件发生,则出事地点的村民们必定联合起来,连续三个夜晚“逐凶”,希望将“散亡”的亡魂赶出本境,以绝后患。第三,无子嗣祭祀供奉。如果家中没有男丁,则无法繁衍后代,自然也就无子嗣祭祀供奉祖宗亡魂。那么,祖宗的亡魂只能成为野鬼。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有子孙送终比有子孙养老更为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含义不仅仅指“无后”而无法养老送终,而且指“无后”而无法顾香火行祭祀。所以,那些无男丁的人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无后的,应急办法有入赘(招上门女婿)、过继(将侄子收归自己名下作为儿子)、两顾(一个男丁日后既祭祀供奉生父母也祭祀供奉养父母或者义父母)。 民间所谓“闹鬼”或称鬼的作扰,其实不过是没有得享祭祀供奉的亡魂在找到子嗣、旁系亲属乃至无血缘关系的人之后,向他们传递出的或强烈或微弱的信息,要求或者暗示他们祭祀供奉。强烈的信息如前者直接加害后者,如惊到、中邪、煞着、缠身,致使其得病或者家运不顺;微弱的信息如前者托梦、显灵给后者以示提醒。在鬼向人传递以上信息的过程中,其信息的强弱与鬼——人关系的亲疏直接相关,呈现出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即以阳间的子嗣为中心点,鬼向人传递索求信息的程度与其跟中心点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关系越是亲近,索求程度越低;关系越是疏远乃至无血缘关系的,索求程度越高乃至肆无忌惮。如上所述,“差序格局”中行动者的行为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血缘纽带作连接的体恤与同情。关系最亲近者如已经得享子孙祭祀供奉的亡魂,有时会托梦给子孙,希望追加祭祀供奉的数量、改变祭祀供奉的方式或者时间地点,因为以往的祭祀供奉常常被其他野鬼抢掠;祖上的“公妈鬼”念及自己的子嗣,为了尽量不作扰子嗣,也只是向后者传递较为微弱的索求信息,虽然是理所应得,如附体在某个子嗣身上向子嗣家里的其他人口语;而对于关系疏远者,鬼在向他们传递索求信息时,由于缺少血缘纽带作连接的体恤与同情,往往动辄威胁加害,致人于不幸境地。对此类野鬼,往往不是通过临时的祭祀可以平息的。而如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野鬼,在礼制上又是不可以定期祭祀供奉的,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 韩愈在《原鬼》中称“故其作而接于民也无恒,故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亦有动于民而莫之为祸福”,就是说鬼有时加害于民,有时造福于民,有时“莫之为祸福”,所以,鬼人之间的互动似乎是无章可循的,鬼似乎也是喜怒无常的。可是,鬼向人传递信息时呈现的“差序格局”,可谓“其作而接于民也有恒”。 三 作为信息沟通媒介的灵媒 灵媒是人鬼神互动的媒介,凡可以传递人鬼神互动信息的渠道或者凭借,皆可称为灵媒。其中为神明附体的“童乩”直接以神明的身份接受人们的“请教”,并以神明的口吻向人开示,这是实现人神沟通的最直接的媒介,在闽粤台等地最为常见,也最为信众接受。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录了当时福建、广东巫觋的流行情况:“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甚。”清代施鸿保《闽杂记·降童》称:“降童即降神也,闽俗又谓之打童,上下诸府皆有之,而下府尤盛。皆巫者为之。”今莆田(属于古时位于“下府”的兴化府)乡间仍称神明附体“童乩”为“上童”,称神明中止附体“童乩”为“退童”。“童乩”本来以男性为主,但在乡村日益“空心化”的情况下,今天的“童乩”大多为乡村中老年女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农村常年在村的人口构成中,女性占了大多数;其次是由于“请教”神明这件事大多由家庭妇女担当;最后是人神沟通时,虽然“童乩”已是神明的代言人,但家庭主妇们在潜意识里还是将其视为一个社会人,还是认为与女“童乩”沟通较为方便,尤其在涉及女性隐私的“请教”事项上。 另外一种灵媒也较为常见,称为“卜杯”。“杯”为生铁铸就,或木雕、竹雕的两豆瓣状器具,分阴阳两面,微凸的一面称阳,微凹的一面称阴。在集体仪式或者个人“请教”神明时,有专人掷“杯”,即在离地面约一米处抛落,如果都是阳面朝上,称“阳杯”;如果都是阴面朝上,称“阴杯”。此两种情况都表明神明对祷告内容持不同意见。其中,“阳杯”最不好,表示神灵对某事持明确否定的态度,没有商量余地。所以,只要出现“阳杯”,就得马上停下来反思片刻,切不可立即又从头开始“卜杯”。掷“杯”人此时兼具释“杯”者的角色,需要向在场的人推测性地说明可能因为某事尚未解决或者准备妥当,所以神明是在提醒我们检点。而如果一阴一阳朝上,称为“圣杯”,说明神明可能同意祷告的内容,但必须连续出现三次“圣杯”,才表明最终获得神明的首肯。如果第一次或连续两次出现“圣杯”,只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为“阴杯”,则前面出现的“圣杯”无效,可以马上从头再“卜杯”。从实际情况看,连续三次出现“圣杯”的概率并不高,也就是说,神明其实是不会轻易对人点头的,不过这样也显示出神明的威严与郑重其事。 “童乩”和“卜杯”是两种常见的“灵媒”,但二者在使用场合、人神沟通效果及人事介入上是存在差异的。选择哪种“灵媒”实现人神沟通,这是大有讲究的。 涉及个人的事务(如久病不愈、家运不顺、生意投资等),大多是通过“童乩”向神明“请教”,而凡是涉及乡村社区公共的事务(如社区内道路修建,元宵节神明起驾绕境巡游的出发时间,下一年度负责迎神、娱神、送神事务的“福首”的产生等),一般是通过“卜杯”“请教”神明。需要向神明“请教”的个人事务都具有隐私及负面性质,当事人不希望与自己家庭有关的负面消息(如受到鬼的作扰)为人所知,如果涉及生意投资,更是需要保密。这决定了其偏向选择“童乩”。当事人只有在“童乩”为神明附体的时候,才会将个人困惑和盘托出,也就是说此刻并没有旁人在场,无隐私泄漏之忧。而如果选择“卜杯”,除神明外,还要面对专司“掷杯”者,“掷杯”者出于“释杯”的需要,可能还需要向当事人询问一些其更加不愿启齿的事情,在此,隐私的保密成为问题。再者,当事人都是带着困惑“请教”神明的,其对从神明那里直接获得信息的迫切性很高,希望神明给出具体的指示,由于原委曲折,神明在听完当事人的陈述之后,有时还需要进一步询问,而这是通过“卜杯”无法达到的效果。还有,“童乩”一般都是在家接受当事人的“请教”,带有宗教私人经营性质,而“卜杯”都是在作为公共空间的宗教场所进行,前者显然更利于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而凡是涉及公共的事务,基本上都是通过“卜杯”向神明“请教”。通过“卜杯”与神明沟通,神明只做“Yes or No”的表态,并不对人事直接指点,人与神明的距离相对较远。在与神明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人得以维持意识的清明。已故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曾精当指出:“在‘大传统’的崇拜中,保持与神祗相当距离,维持个人意识的‘清明’很重要……注重对文字符号的理解力而鄙视与神直接沟通的精神恍惚状态。”他认为,在“大传统”的崇拜中之所以鄙视与神直接沟通,是因为人们对神的敬畏之心大于亲密之情。不过,李安宅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鬼神卜筮这些东西是要个人自用,或为民上者用的。他们尽量藉以愚畏百姓都不要紧,在下头的却是不准谣言惑众的。《王制》说:‘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这也是孔子说的“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含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非常强调人的地位、人的能动性,是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者。在儒家的“大传统”里,是需要维持个人意识的“清明”的。 在“卜杯”的过程中,出现“阳杯”和“阴杯”的机会是非常多的,而“卜杯”又往往是在仪式性的场合,在场见证的村人众多,这时,“掷杯”者如何“释杯”变得极为重要,即出现“阳杯”和“阴杯”的时候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释、如何寻找出在场众人可以接受的原因。所以,担当“释杯”者基本上都是乡村社区的民间权威,其谙熟社区事务,处事兼具通情达理知法的本领,讲话可以服众。当出现“阳杯”的时候,“卜杯”必须暂停,“掷杯”者需要寻找出导致神明不愿首肯的可能原因,例如,与某项公共事务相关的人和事是不是没有处理好公私关系?是不是损害了别人家的利益?“掷杯”者提出可能的原因之后,即通过“卜杯”请示神明,如果神明首肯,即当场宣布相关人员必须按神明的旨意改正;如果神明没有首肯,即需要继续寻找原因。“掷杯”者常常说“神明有时也让人且主意”,意思是说神明有时候也允许人暂且先提出某项主张。这既有“人”借“神”威的企图,也有人维护神明脸面的动机。我们看到在此过程中,神明是无言的,人其实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并借着神明的名义,主张公道,调解矛盾,致力于社区公共事务。这可视为在人神关系中,人维持自身的“清明”意识的一种努力,也是民间宗教在集体性仪式活动(与宗教私人化场合相比)中与中国的“大传统”具有更直接关系的一种表现。在集体性仪式活动中,人神关系事实上不是个人与神明的关系,而是集体与神明的关系,个人无须虑及个体行为失当而触神怒。在此意义上,民间宗教并非神秘迷狂,以“迷信”来统称中国的民间信仰其实是不科学的。 不同的灵媒决定了人神互动的不同模式。在以“卜杯”为灵媒的人神互动中,神明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给出的信息并非预测型的而是决断型的;在以“童乩”为灵媒的人神互动中,神明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咨询师”的角色,给出的信息并非决断型的而是预测型的。决断型的信息发出之后只存在是否权威的问题,预测型的信息发出之后则存在是否灵验的问题。基于对神明的期盼和人的好奇心的驱使,人们更愿意关注预测型信息的灵验程度,预测型信息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四 神圣信息的传播规律 在以“童乩”为灵媒的人神互动中,人神关系是个人与神明的关系,神明提供给个人的是预测型信息,我们姑且称之为神圣信息,以区别于人际世俗信息。因为在信息的传播上,凡圣的确有别。世俗信息传播的特点是人们常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神圣信息传播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个人通过“童乩”向神明“请教”,请求神明驱邪解厄,同时向神明“许愿”,即如果神明的指点、预测应验,当及时酬谢神明。个人对神明的“请教”“许愿”,事实上是在个人与神明之间建立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实际的“代理人”其实是“童乩”。当事人对神明的酬谢仪式是在“童乩”家里举办的,当事人只要交一笔钱,“童乩”就可以帮当事人“做道场”,这成了宗教经营活动,也有学者称之为“灵力经济”(the economy of magical power)。从“童乩”的角度看,显然需要时刻维护并提升附体于其身上的神明的“灵力”。 按照陈纬华的定义,“灵力”(magical power)指神明能感受人们的祈求而有所回应的能力,亦即感应力,是某一神明或整个民间信仰能否生存的关键。神明灵不灵的判准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灵力”并非自然状态的产物,而是人为的结果,每一尊神明的“灵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忽兴忽衰的动态变迁的状态之中。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也认为:“‘灵’是一个由社会制造出来的概念,就像声望这个概念一样,它是外在于个人动机活动之外的。”“灵力”的确是社会性的,也的确是忽兴忽衰的。不过,“灵力”的兴衰大体上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是有规律的。而且,与其说“灵力”的兴衰是“童乩”经营的结果,不如说是信众以口头传播参与“灵力”的建构、用双脚投票导致“灵力”的解散。 在今天福建莆田的乡村里,对特定信众来说,“童乩”的“灵力”兴衰周期大概在三年左右。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各路信众你来我往,不绝于寻访愈来愈远的他乡“童乩”的遥遥路途。本村“童乩”的灵力虽然早已息微,但却丝毫不妨碍他乡的信众趋之若鹜。民间一直有“近庙气神”“照远不照近”“贵远轻近”“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等说法,都是指神明与信众的关系似乎是反“差序格局”的,即距离越近,关系越差,距离越远,关系越好。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信众通过“童乩”向神明“请教”,一定存在灵验的概率问题。信众对灵验与否的反应,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果不灵验,信众一般不会怪罪神明,而会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导致不灵验:一是“童乩”变质污浊,神明已经不愿附体其上,所以从“童乩”口中出来的预言已经不代表神明的旨意了;二是出于信众自己的原因,或者求神的内容可能要求过分乃至有悖常理,或者当事人前世或祖上罪孽深重而得不到解脱。可见,信众如果对不灵验的事件加以传播,首先会让自己以及家庭蒙羞,同时也有损神明的名义,是对神明的不敬。所以,信众对神明是否灵验的信息采取选择性传播的策略,凡是灵验的信息,就积极传播,这既表明其得到神明的护佑而脸上有光,同时在广为传播的过程中也荣耀了神明;凡是不灵验的信息就小心屏蔽,既不到“童乩”家里向神明“还愿”,也自觉防范不灵验信息的外泄,做到“坏事不出门”。这样,在广大信众中传播的都是关于神明灵验的信息,更何况传播灵验的神圣信息这个行为本身,相当于以实际行动赞颂神明,所以,信众往往奔走相告,偏向于作夸张传播,众人参与神圣信息传播的再创作,或添枝加叶,或添油加醋,神明愈益活灵活现。 信息经济学和传播理论都对作为社会生活现象的信息传播行为作出解释,信息经济学认为,“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息的刺激”;而传播理论也注意到了选择性传播的现象,“尽管传播中的个人以某种方式共同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是经参与其中的个人各自的头脑筛选并制作而成的”。参与神圣信息传播的信众尤其明显地受到获取和传播神圣信息的刺激,并进行了选择性传播。 一个人被神明附体而成为“童乩”的过程一般是悄悄发生的,既没有公开的仪式,也不需要正式的宣布。这跟台湾地区的情况不同。在台湾乡村,成为聚落公认的“童乩”是需要经过“关童乩”“坐禁”“落地府”“过火”等复杂而公开的考验程序的。之所以有此差别,大概与大陆乡村经历过革命风潮的激荡,“童乩”活动曾经地下化有关。 如果以一个被神明悄悄附体的“童乩”为同心圆的圆点,这个同心圆的结构可以划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外圈层。第一批信众一定是“童乩”所在的本村村民或者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他们属于内圈层并最先向被神明附体的这个“童乩”“请教”。当他们将灵验的神圣信息往外即中圈层传播时,他们也暗中将其遭遇到的不灵验信息屏蔽掉。当不灵验的次数累积到一定地步时,或者说不灵验的概率超过灵验的概率时,信众就可能逐渐放弃对该“童乩”的信任,转而向身边的人打听其他灵验“童乩”的情况,这可以说是信众用脚投票选择“童乩”,类似于宗教学上所谓的“改信”(conversion)。不过,从信息经济学的原理解释,也许可以看得更透彻,即“最大化的预期效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其中的预期是根据个体本身的概率计算的”。如果灵验的概率过低,信众就会放弃对该“童乩”灵验的预期。对内圈层的信众来说,从对本村“童乩”的“请教”开始到其放弃对该“童乩”灵验的预期,这个过程的长短就是“童乩”灵力兴衰的周期(相对于特定信众而言)。这个周期其实是指特定信众在该时段内累积的不灵验概率已经超过了灵验的概率。如果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句话来比喻“童乩”灵力的兴衰,那么,一旦内圈层的信众对“童乩”不抱灵验的期待,则表明墙内开的花变得不香了。并非墙内的人一直闻不到花香,也并非这堵墙固若金汤,随着花香的飘散,墙也会移易,墙外的人也会变成墙内的人。花香一直往墙外飘,而墙也随香外移,原身处墙外的闻香者成了墙内人。就是说,内圈层的信众尽管弃“童乩”而去,但他们传播的灵验的神圣信息却不停地往外围即中圈层传播。当中圈层的信众接收到灵验信息时,就会“翻墙”从中圈层(“墙”外)来到“童乩”所在的内圈层(“墙”内),将此前被内圈层信众抛弃的“童乩”重新奉若神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圈层的信众也会弃该“童乩”而去,而外圈层的信众也有一天会接收到“童乩”灵验的信息,从远处来寻访“童乩”。 由上可见,神圣信息的传播机制是以“童乩”为同心圆的圆心,其周边首批信众为其灵验信息传播的内圈层。由于内圈层的信众对灵验的负面信息进行自我管制和过滤,使中圈层的信众处于负面信息的屏蔽状态,只从内圈层接收到正面的灵验信息,从而建构出“童乩”灵验的正面形象。等到中圈层的信众累积出灵验的负面信息之后,又对灵验的负面信息进行过滤并只将正面的灵验信息传播给外圈层的信众。依此类推,使“童乩”灵验的声名次第远播。 灵验的神圣信息传播的速度取决于信众之间口传的速度,而口传的速度取决于信众互动的频度与半径范围内活动的可及性。随着机动交通、移动电话、智能手机以及微信等自媒体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普及,信息扩散的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某地“童乩”灵验的信息常常不期而至。同时,在同样的时长里,信息传播的半径范围也远超从前。其后果就是作为外围的信众从内圈层或者中圈层接收到灵验信息的频率加快,信众累积不灵验信息的周期趋短,这也意味着“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趋短。不过,可作弥补的是,由于信息传播半径范围扩大,导致圈层范围和信众规模扩大。我们假定一个“童乩”接受信众“请教”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更大规模的信众群体就需要在更长的时段里才能分别累积出超过灵验概率的不灵验概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尽管神圣信息传播的半径范围可能超过村民日常的社会交往范围,但对“童乩”来说,其潜在信众分布的半径范围毕竟是有限度的,信众寻访“童乩”的最大半径范围,一般在机动交通工具(如摩托车)可当天往返的距离之内。所以,从总的趋势看,“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将趋短。 与神圣信息传播规律、“童乩”灵力兴衰周期相应的是“童乩”灵力兴衰的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童乩”的灵力辐射半径由近及远。在空间上,“童乩”灵力的覆盖面并非呈圆形(内圈层除外)或扇形,而是呈圈层结构;在时间上,“童乩”灵力只有在内圈层的辐射力衰退之后才进而辐射到中圈层乃至外圈层。 五 余论 从信息隔绝、信息需求、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信息传播的角度研究民间信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人鬼神之间互动的规则,也可以更容易获得内部视角靠近信众的心理世界,发现民间信仰实践的轨迹。 民间信仰作为乡村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简单地将其斥为“迷信”“愚昧”,显然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民众行为逻辑的理解。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信仰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民间信仰研究亟需开出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的取向。目前已有的宗教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经由对制度性宗教的研究而创发的,而中国民间信仰属于“弥漫性宗教”,已有的宗教学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我们需要发明基于中国民间信仰活动的一些概念(如“神圣信息传播”、人鬼关系的“差序格局”)或者中观层次理论,让民间信仰成为可以理喻的日常活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现代舆论对民间信仰的污名化,拓展现代人对民间信仰的理解。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6期,略去注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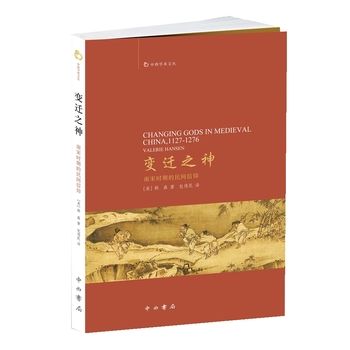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