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程乐松
作者简介: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
原发信息:《世界宗教研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116-124页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鬼的观念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道教以不死为信仰的旨趣,必然要面对死亡与鬼的基本观念。然而,从观念内涵和历史变迁来看,鬼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从鬼的观念历史演进入手,将鬼的意涵分梳为陌生的超自然力量和对疾病与死亡的焦虑。以此为基础,分析鬼这一本土观念与道教信仰实践的结合方式,围绕着长生与生活秩序理解道教如何处理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鬼的观念及其带来的信仰焦虑。
关 键 词:鬼/观念史/炼度/长生
道教的信仰实践是在死与不死的观念张力中展开的,死亡是道教信仰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要理解道教关于死亡和不死的诠释,鬼这一复杂观念的历史就是不能回避的课题:一方面,需要梳理鬼观念的演变过程,理解道教信仰的观念环境;另一方面,从道教信仰的内部出发,分析道教如何诠释和应对以鬼为具象的死亡,如何实现从死亡到不死的超越。
道教的鬼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亡故的人变成的鬼,即人死为鬼;其二则是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且对生活和生命有负面影响的超自然力量,疫病之鬼、干支之鬼等。在道教的信仰实践中,这两种鬼都需要被谨慎处理:从疗疾到普度的不同层次都可以看到信仰实践对鬼的诠释和应对。通过这些诠释和应对,分梳为鬼从陌生者和有害者、乃至受害者转化为长生者,被带入长生的状态,最终将鬼所承载的人的死亡消解在信仰实践之中。
一、鬼的双重意义:陌生与死亡
谈论鬼的含义,学界大多会征引《礼记》中广为人知的说法: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者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①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②
据上引材料,人死之后就变成鬼,包括“鬼者,归也”③这样的说法都有类似的意涵。此外,“事鬼神”的“事”是指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鬼的具体方式。在《礼记》中所见的“事”就是敬畏的态度和祭祀的行为。
然而,鬼的原初含义是指生活世界之外或地理界域之外的陌生者,这与古代中国关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想象有关:来自域外的陌生人被称为鬼。王国维先生《鬼方混夷玁狁考》中就指出,“伐鬼方的高宗,就是商殷的武丁,而鬼方就是指獯鬻、玁狁、匈奴。(出易经,既济(九三)、未济(九四))”。④与此相对,章太炎先生的讨论则更为深入。他在《小学问答》中讨论“夔神鬼虚也”时详细说明了鬼的观念缘起:
古言鬼者,其初非死人之神灵之称也。鬼宜即夔。说文言鬼头为田。禺头与鬼头同。禺是母猴,何由象鬼,且鬼头何因可见?明鬼即是夔…魖为耗鬼,亦是兽属,非神灵也。韦昭说夔为山缫,后世夔做山魈,魈亦属兽,非神灵…故鬼即夔字,引申为死人神灵之称。⑤
对照《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鬼头”⑦,这一部首与畏、禺等字的意涵有关。《说文解字》将“畏”及“禺”分别解为,“畏:恶也,从田,虎者。鬼头而虎爪,可畏也”、“禺,母猴属,头似鬼,从田,从构”。⑧
关于“鬼”字的词源学和语义学讨论,最为周详的研究当属沈兼士先生的名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沈兼士先生的研究将鬼的意涵归拢到以下两个层次:其一是域外的人类和类人异兽,是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陌生者;其二是人在生命消亡之后的存在形态,这是生命状态上的“陌生者”。这两个意涵既有差异,也有共通之处:从日常生活出发,异质的陌生者都是焦虑和恐惧的源头,都需要信仰性的技术和实践应对。
与词源学的讨论相对,还可以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理解鬼的内涵。王充在《论衡·订鬼》一篇中讨论了鬼的观念内涵:其一,鬼是人想象出来的事物,由于疾病或独特的精神状态而造成的想象;其二,鬼是邪恶之气在人身体中的体现,也可能是事物的精气;其三,是天亡的人变化而生成的事物;其四,是自然之物变化的产物,因此鬼的形貌也是可以变化的;其五,鬼就是域外的异兽或域外文明中所见的人类。
由此,鬼是一个集合名词,并不特指某一个事物,也可以是某种气。鬼是指某一类事物——陌生和异常者。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看,鬼是指在生活世界中可能出现的陌生者——无论是域外的类人生物和人类,还是在自然界和身体中出现的异质且善于变化的气。鬼的观念是以古代中国观念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气”与“变”的观念为基础的。从具象化的鬼到抽象的气,气的引入一方面解释了鬼的源起和行动机制,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应对鬼的方法。这一变化使得鬼从具体的对象转向了抽象的观念,从而与古代中国的生命观念联结在一起。
这些难以捉摸的陌生者之所以成为人们关切乃至焦虑的对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随时可能进入了日常生活,时刻威胁着人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莫名伤害的可能性。由此更增加了人们对“鬼”的焦虑感。
由此,理解鬼的内涵,就需要引入“气”、“精”、“怪”和“变”等观念。不同存在样态的鬼、怪、精之间存在着内在共通性——即气的变化。气是生命的基础和实质,生命的载体也会随着气本身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转移。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变化的观念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十分常见,试举《淮南子·俶真训》的记载说明。
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护而入觇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⑨
上文强调了神变和形化的内在关联,内在于生命之中的神决定了外在的身体形象及性质。神的变化和衰竭就会引致身体的变化。与此相对,另一种变化的观念则与时间相关,一个事物存在的时间足够长之后就会转变为另一个事物,例如《礼记.月令》中描述的:
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之数至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麦之为蝴蝶,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无知化为有知而气易也。⑩
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论及“变形规则(law of metamorphosis)与生命综合”时讨论了时间与生命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生命是不断连续的整体,不同生命领域无固定的形态,一切事物都可以相互转化。”(11)在《抱朴子内篇对俗篇》就可以看到:
千岁松柏,四边枝起,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清犬,或如青人,皆寿千岁。……又云:蛇有无穷之寿。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猨;猨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寿千岁。蟾蜍寿三千岁,骐麟寿二千岁……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满五百岁者,其色皆白,能寿五百岁则能变化;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潜变为人形。(12)
依照一定的时间规则,事物逐步具备了变化的能力。其中部分的动物就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可以转变为人的形貌。正如胡司德(Roel Sterckx)在其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不从本体和结构上区分生物,因此,战国两汉时期的文献宣称: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矿物,都缘起于从不间断的变化和变形…古代中国文献中涉及了许多形式的动物变形:由报应导致人变为兽的“怪变”,有随着四时节奏更替而变形的动物,还有自发变形的动物……许多动物的变形也可以视作人间事物变化或宇宙周期变化的征兆。”(13)
李丰楙将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归结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变化神话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反映中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即是正常的生殖、自然的死亡,正常的处理就不会发生变化;反之,对于终极关怀的冤怨意识,就会形成以变化来延续生命的方式,以弥补、顺遂其未竟之愿,可知变化神话是与中国古代的魂魄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4)
李丰楙认为,变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古中国一片茫茫苍苍的生活世界中,自然形成的神话文化体现了人们采用拟科学的观察、隐喻关系的联想以及哲学式的思辨,一探宇宙万物的生成奥秘的愿望……是人类自有意识,感觉就拥有的思维习惯……一种原始、野性思维,最后经由哲人的再思考,才形成一套解说的理论架构。”(15)从思维习惯到理论架构,最重要的过渡就是观念的介入。这些不同类型的变化背后都有独特的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气”为中介,以“人形”为特征的变化——即从物到怪和妖的变化。据《法苑珠林,卷四十二.妖怪篇·第二十四》引干宝《搜神记》卷一及卷二篇首语: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16)
以精气解释变化,同样的精气有完全不同的展现形态,并且在不同形态之间不断转化,这是对变化观念最典型的解释。与《搜神记》的说明相较,《抱朴子内篇·黄白篇》中的解释更为清晰:
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盖人身本见,而有隐之之法。鬼神本隐,而有见之之方。能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其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鼋,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17)
变化被视作天地之间自然的过程,而天地之间万物的变化模式都是与气的变化方式一致的,定形与变形的接续是事物的实际存在模式。从气的变化到变形,直至生命形态从物变成动物,从动物变成人,成为合理的过程。
通过对生命缘起、存在形态及变化过程的描述,引导人们理解人死之后的身体与生命变化,进而指导祭祀仪式和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陌生死者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鬼的理解就涉及到生命、魂魄及神气的诠释。之所以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鬼字内涵的分化,是要明确鬼与怪、精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尝试说明其背后共同的生命观念。此外,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陌生者,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源头,更是对不同日常生活境遇的诠释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鬼、怪和精等概念在面向日常生活时的异质性并没有因为语义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鬼、怪、精,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时出现的异质且意图不明的力量,可以被视为一种令人焦虑和恐惧的陌生者。具体到鬼这一观念,陌生的意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死者与生者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对于生者而言,亡故者都是异质的存在,谨慎地对待亡故者是保证其平和地与生者相处的关键,这就需要严格执行祭祀活动;其二,同样是作为死者的鬼,也有熟悉与陌生的区别。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应对不同类型的鬼和灵性存在。体系化的应对方式足以消解对异质性的陌生者的恐惧和焦虑,通过祭祀和信仰技术,将这些异质性的存在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可控的因素。由于这样丰富的诠释空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不时面对与鬼打交道的问题,处理在生活常识体系中被认为是由鬼带来的问题。
二、疫病、鬼祟与击鬼:生活中的信仰技术
上文的分析将源流复杂的鬼观念聚焦于“人死为鬼”及“生活世界中的陌生者”这两个要点上。鬼的所指仍然需要考虑具体语境:身体内的鬼、自然之间的鬼物与鬼气,在墓中出现的魍魉,这些都是与鬼的性质一致的存在物。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乃至不同的信仰实践中,鬼的内涵都在随时发生变化。
那么,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实践体系中,鬼的存在形式及其与日常生活发生关联的机制是什么?按照武雅士(Arthur P.Wolf)的说法,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超自然力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神、鬼与祖先。(18)这三种超自然力量的功能和定位都有差异,其中鬼的功能和与生活的互涉方式最为复杂:“神和祖先会得到社会长者的尊敬,而鬼像乞丐一样被鄙视。神和祖先被求助于保护和帮助,而鬼除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之外,不能给人提供任何东西……在中国的玄学(神秘知识)中,人性中积极、无形、属天的一面被称为神,消极的、有形的和属地的一面被称为鬼。哲学家将神与发展、生产、生命,从而与光明和温暖联系在一起,而鬼等同于衰退、毁灭和死亡,引申开来等同于黑暗和冷漠……若将由鬼造成的人类的痛苦编成一个目录,则这个目录会十分冗长,包括意外事故、不育、死亡和各种疾病,以及庄稼歉收、生意亏损,乃至赌博中的厄运,这些都可以归在鬼的身上。”(19)这一方面说明了鬼在解释日常生活境遇时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鬼在日常生活中多样化且颇具神秘感的存在形态。与此同时,这里所提到的鬼并不仅仅指亡故的先人,而是泛指在生活中出现的超自然力量。这些超自然力量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形式主要有鬼祟、疫病与祭祀三种。
作祟的鬼既可以是外来的,也可以是内在于身体的;既可以是亡故的先人,也可以是陌生的亡者;甚至既可以是亡故的人,也可以是在生活中遭遇的超自然力量。
鬼能作祟的观念在秦汉的时期就十分流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就作祟的鬼与疾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较为细致的解释,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庚辛有疾,外鬼伤死为祟……壬癸有疾,母逢人,外鬼为祟。(20)
亡故的先人作祟造成生人的疾病和灾祸。从考古资料看到,包括镇墓文及镇墓瓶的铭文都十分明确地强调人鬼殊途,生死两不相干的观念。(21)
按照《太平经》的说法,鬼是天地自然之间的流行和游走的超自然力量,带来灾害和疾病,
天地大多灾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复有风湿疽疥,今下古得流灾众多,不可胜名也。(22)
天地之间的灾害和疾病都可归因于作祟的鬼,这种观念在道教信仰中不仅可以起到解释病因的作用。在《太平经》中,鬼也可以与神并列,出现在身体之内,
天地之性,精气鬼神行治人学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阴,精者居人肾阴,鬼者居人肝阴……凡人腹中常阴念恶,故得恶应,不能自禁。咎在常阴念善恶,鬼神因而趋善恶,安鬼于此可验矣。(23)
鬼在人的身体内与神一样司察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对人的伦理性约束。
善为祟的鬼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人们常见的病归因于作祟的鬼。一旦作祟的鬼成为病因,那么疗疾的过程自然就是驱鬼或杀鬼的仪式。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流行的疫病。按照汉代刘愍《释名》中对“疫”字的解释“疫者,役也。言有鬼行疾也。”(24)行疾应该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导致疾病,另一种则是使疾病流行。疾病的存在和流行就必然带来应对鬼神,特别是鬼的信仰技术和实践。治疗某一疾病的方法就是驱赶造成这一疾病的独特的鬼。疗疾就是驱鬼。(25)
除了疾病和疗疾之外,生活中可能遭遇鬼的场合都需要固定的应对方式,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所见的击鬼方法,
人毋故而鬼惑之,是(上攸下羊)鬼,善戏人,以桑心为丈,鬼来击之,畏死矣。(26)
这里所见的鬼是“善戏人”,而不是带来灾祸。可见在秦汉时期,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识体系中,鬼是广泛存在的,其种类和存在形态十分复杂,其功能和表现形式也不同。换言之,人们需要与鬼打交道的基本技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鬼实际上就是可以随时遭遇并且需要谨慎应对的超自然力量。
简言之,在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鬼是无处不在的焦虑,随时可能入侵和干涉人们生活和生命的鬼内涵复杂、存在形态多样。鬼就是生活中引发焦虑的陌生者,也是生活与生命的威胁者。当然,除了代指难以捉摸且弥漫在周边的超自然的陌生力量之外,鬼也可以指代亡故的先人及熟人,乃至其他的陌生人,这些鬼是生人转化而来的,他们的生活经历及活着时候的社会地位会直接决定他们的角色,以及人们应对和处理他们的方法:一般而言,亡故的先人需要定期的祭祀,而熟人社会中其他的亡故者则会在各自的家族祭祀中得到处理,与之相对,熟人社会之外的亡故者就是比较神秘和危险的,需要更加谨慎的应对。
作为日常生活中十分活跃的信仰形态,道教也必须提供应对生活中的陌生者的技术和实践方法,以及符合生活常识的诠释。当然,道教对于鬼的处理也体现了其信仰的特色:一方面,道教通过关于鬼的存在形态及分类模式的解说,诠释了鬼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并提出咒鬼和杀鬼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应对生者对于亡故者和自身亡故的焦虑,将鬼与不死连接在一起。通过对于死后世界的解释,结合道教对于生命与身体的修炼实践,将死亡的鬼转化为长生的仙,从而达致从鬼到仙的跨越。
三、仙途:咒鬼、鬼仙与炼度
道教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用独特的科仪和实践技术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陌生者,另一方面在于用神学诠释和具体实践消解人的死亡,让死亡直接指向了长生。这也体现了不死和长生作为道教信仰旨趣的特色,进而言之,对于道教信仰实践中的参与者或者普通的民众而言,生活中的陌生者(超自然力量及陌生的亡故者)以及先人与自身的死亡构成了独特的双重焦虑,道教信仰就是通过诠释和实践消解这种焦虑,让生活世界保持稳定且可预期的运行节奏。由此,可以从咒鬼、鬼仙与炼度三个层次讨论道教对于鬼的处理,特别是对于死亡的消解。
鬼的谱系与天地结构、时空乃至地域、日常生活都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性使得道教信仰可以依照鬼的谱系诠释个体的生命境遇,也可以诠释周期性的灾难,乃至在不同区域中出现的灾害及疫病。以南北朝时期的《正一咒鬼经》为例,其中详细描述了鬼的构成、分类及引致的殃祸,并在道教科仪实践的整体框架内说明了应对鬼的方法:
谒请素车白马君五人,兵士十万人,主收某家宅中三丘五墓之鬼。谒请运炁君五人,兵士十万人,主收某家宅中百二十刑杀之鬼……谒请刺史从事千二百人,各官将五人,兵士十万人,主收某家宅中五方瘟疫炁剔人之鬼。谒请无上太和君五人,兵士十万人,主收某家宅中百二十祆魅邪道之鬼。(27)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鬼构成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世界并行的异质力量的世界。由此,家庭生活和个体生命时刻处于鬼的威胁之中,(28)需要科仪保障其生活的安全。
除了在日常生活可能出现的威胁之外,按照《正一咒鬼经》的说法,处理和应对鬼的存在也关涉到信仰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天师曰,欲行道法,欲治身修行,欲救疗病苦,欲求年命延长,欲求过度灾厄,欲求白日升天,欲求宅舍安稳,欲求田蚕如意,欲求贩卖得利,欲求奴婢成行,欲求仕宦高迁,欲求讼词理诉,欲求男女命长,欲求保宜子孙,欲求妇女安胎,今为别请十部都曹,正炁中即,刺史从事,素车白马君,北城韶命君,天上督逆君,广司君,太玄老君,太和之炁一千二百人,各将军五人,屯住某家中庭,兵刃外向,监察内外下官故炁,血食之鬼,祆惑之神,众精百邪,千鬼万神……五毒之炁,藏在宅中不肯去者,伏惟太上勑下天曹,应咒斩杀之。(29)
按照上述引文,鬼是生活和信仰实践中“不正之气”的一种,想要通过其他信仰实践得到生命境界的提升乃至长生,就需要首先保障不受“不正之气”的侵扰。鬼被纳入到一个更基础的观念体系之中——都被认为是气的一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的应对手段仍是请官监察震慑不正之气。
道教信仰从不同的观念视角建构鬼的谱系:
有病苦者告诸弟子大一太玄元始炁三十万亿诸国祭酒,今牒中国诸姓字,依名杀之,若有居诸山鬼林鬼,草鬼木鬼,冢鬼墓鬼,家鬼他鬼,水边鬼道傍鬼……呼唤人鬼,伤人鬼,嗔恚鬼,急疾鬼、行病放毒鬼,五瘟鬼剔人鬼,有急咒之,鬼自摧灭。(30)
从信仰意义上看,鬼的广泛存在是对严谨行为、努力实践的督促。无时无刻都存在的现实的威胁以及生活与威胁之间的紧张冲突,对于信仰者和实践者而言,就是持续信仰实践的动力和保障。
《正一咒鬼经》还强调,鬼的谱系性知识、了解司察鬼的神明也是应对鬼的有效手段:
正一真人告诸祭酒弟子,若能受吾是经,有急头痛目眩寒热不调,常读此经,魔魅破碎,不敢当吾咒也,若有官狱水火之灾,亦读此经,宅中有鬼亦读此经,元君讳字当读是经,有诸高大广长鬼神苦挠天下,暴酷百姓,鬼神行病,鬼神行疫,鬼神行炁。……一切大小百精诸鬼,皆不得耗病某家男女之身,鬼不随咒,各头破作十分,身首糜碎。当诵是经,咒鬼名字,病即除差,所向皆通。(31)
知晓神灵的名讳,并且咒念鬼的名姓就可以直接打到却病禳灾的效果。从鬼的谱系到请官煞鬼,直至咒念驱鬼,超自然力量与生活世界的关涉就可以被纳入到威胁与抵御、隔离与并行的信仰结构中,并且突出了道教信仰技术和科仪实践的重要性。与日常生活相伴的信仰实践,让鬼从陌生的焦虑到可以应对的威胁,进而消除威胁。
除了陌生的超自然力量之外,鬼的另一个重要意涵就是亡故的人。以长生为旨趣的道教,必须处理鬼与死亡的本质问题,即人的死亡和人死为鬼到底以为着什么?对于道教信仰而言,死亡是可以被消解的。消解死亡的方式有如下三种:其一是认为死亡只是走向长生的一个环节,某些人获得长生的方式就是暂时的死亡;其二则是通过描述和诠释地狱的结构及行为规范,说明进入地狱的人如何通过自身的信仰和努力重获生命,乃至实现长生;其三强调通过科仪实践为进入地狱且没有修行基础的人提供了普遍长生的仪式解决方案,保障亡故了的人都有明确的重生和长生的方法与渠道。
在修仙技术中,与暂时死亡关系最密切的是尸解法。按照《抱朴子内篇·论仙篇》所描述的仙等结构,尸解仙是对应尸解法的一个仙等。尸解是以常识意义上的死亡为基本形式的长生之道。对于观察者和生人而言,通过尸解长生的人的确已经死亡,而对于尸解者而言,死亡不过是一种假象。在早期的道教观念中,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关于亡者长生的描述,即“暂过中阴”。《老子想尔注校笺》注“死而不亡故寿”一句时提及了“暂过太阴”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道人行备,道神归之。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故寿也。(32)
在《想尔注》的描述中,托名死亡的实质是修行者暂时经过太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想尔注》重新诠释了“死而不亡”的内涵,死与亡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生命状态。死而不亡的内涵改造了在生活常识中的死亡观念,也为死亡和亡者达致长生提供了观念上的空间。暂过太阴的人并没有亡,而是以死的形成持续面向长生的实践。死亡的诠释总是以生命的理解为基础,生命的构成方式及层次结构直接决定了如何认识不同层次的死亡。身体与生命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具有弹性的关系。真正的死亡就是魂魄及体内神与身体的彻底分离,这就为死亡的诠释提供了空间。
除了神秘的生命观,道教的死亡诠释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地狱观。地狱的形象及运转方式,乃至权力结构,都直接关涉亡故者的处境和命运。检视藏内文献,可以看到鬼仙、南宫受炼与普度是解决亡故者长生问题的基本模式。《钟吕传道集》描述的仙等结构中,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等五个等次。鬼仙是最下等次的神仙:
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无关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回,又难逢蓬瀛,终无所归。止投胎就舍而已。(33)
鬼仙实际上是在鬼与仙之间的生命形态,以最基础的方式达致生命的存续。与之相对,比较常见的是地下主、鬼帅,以及地狱中“南宫”受炼等观念。在陶弘景的《真诰·稽神枢·卷十三》中提及地狱中亡故者与地下主、鬼帅及南宫受炼的诸种说法。(34)地下主和鬼帅通过尸解的方式进入修仙的阶次,在不断的修行过程中逐步提升在仙界的等次。
此外,道教应对亡者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则是普度科仪。普度一方面是指救度普通的亡故者;另一方面则是指救度地狱中所有的亡者。(35)以炼度为基本手段的普度科仪的目标就是救度地狱中的亡魂,让他们得以超脱地狱,皈依道教并达致长生。这一方面体现了道长自身的修炼和功德的累积;另一方面,也是在科仪之中积累功德的手段。
《灵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黄缯章法》(36)中细致说明了炼度的对象,以及炼度的方法及其程序:“承元始大化,诸天开宥幽牢地狱三涂五苦饿鬼死魂,并出长夜,一切光明。皇道既陶,死骸还人,三界清肃,土府太平。请以灭度,托尸太阴,寄形地官,功微德少,未蒙者皆女青符命,随所统领,安慰抚恤,供给营卫,不得摇动,使还托生人身。是时诸天大圣众……今承女青上宫旧典,申明圣道,为某郡某县乡里清信弟子男女某甲,年若干岁,本命丙午,赤帝领籍,七月受炁,丹天禀阳,先功未满,履在秽世,尘浊所染,应在灭度。托命太阴,寄形土官。今于中天某乡里中安宫立室,以为住止。功微德少,未能自还。今为土府所见驰逼,不相容安,魂飞魄扬,尸形无寄。谨依明真大法金篆玉书之文,上请诸天自然玉字女青符命,告下某天中九土灵官,安镇某甲身形骸地宅……应转者转,应度者度,应生者生,应还者还。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抚恤营卫,不得摇动。”从上引的段落中可以看到,炼度仪式是为某一特定的亡故者实施的,其目的就是让亡故者脱离地狱,回归生命状态。
与此相对,道教的科仪体系中还有面对一切地狱亡魂展开的普度仪式,普度仪式在唐宋以降的道教科仪中十分常见。《太极祭炼内法》中将普度仪式和祭炼法溯源至葛洪,并解释了何谓祭炼。
太极祭炼内法者,葛仙公祭鬼之法也。人死魂升而魄降,是其常也。其变也,则有魂魄不能升降,而沦滞于昏冥之中。其饥渴之欲,幽暗之识,茫茫长夜,无有已时。是以仙翁悯之,在法中有祭炼之道。所谓祭者,设饮食以破其饥渴也。所谓炼者,以精神而开其幽暗也。至使沦滞之徒,释然如冰消冻解,以复其本真,则其法大矣。(37)
简要梳理《太极祭炼内法》的科仪程序和内容,其基本原理就是以道士的内炼之气调动天地之气,通过施食和炼度恢复死亡之前的身体,在皈依道教信仰之后即可脱离地狱。
道教应对鬼的信仰技术和实践体系是十分完善的:从咒鬼到鬼仙、直至普度,无论是陌生的超自然力量还是亡故的人,都是围绕着生活世界的需求展开的。一方面,陌生的超自然力量形成的与日常生活平行的鬼的谱系,给生活世界中的人带来了对于陌生力量的焦虑,咒鬼和杀鬼是保障生活世界秩序和平静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面对亡故的先人及陌生的亡者,乃至生人自身死亡之后的焦虑,从南宫到炼度的系列信仰手段保障了死亡从信仰技术的意义上转化为长生。从古代中国的鬼的观念到道教信仰体系中的鬼,道教用自身独特的生命观念及宇宙图景融入了鬼的谱系和观念,并且通过严格的道法实践将鬼承载的陌生者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转向生活世界的秩序和生命的长生。
①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672页。
②同上,第814页。
③钱穆:《论中国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收入氏著《灵魂与心》,九州出版社,2011年。
④王国维:《鬼方混夷玁狁考》,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1-1961年,第583-606页。
⑤掌太炎著,殷光焕校点《小学问答》,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
⑥⑦⑧许慎著,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5年,第186页。
⑨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40页。
⑩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第216页。
(11)卡西勒(Ernst Cassirer),An Essay on M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第66-67页。
(1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13)Roel Sterckx,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2,p.203.
(14)李丰楙:《正常与非常:生产、变化说的结构性意义》,收入氏著《神化与变异: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中华书局,2010年,第83页。
(15)同上,第127页。
(16)释道世撰,周书迦、苏晋仁校证《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974页。
(1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93页。
(18)武雅士:《神、鬼和祖先》,收入武雅士编,彭泽安、邵铁峰译《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仪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19)《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仪式》,第173-174页。
(20)关于古代中国鬼与生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丧葬仪式中的运用,参见林巳奈夫:《汉代鬼神の世界》,《东方学报》(第46册),1974年;另见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以及氏著《〈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还可以参见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缘起》,《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王育成:《东汉天帝使者与道教的缘起》,《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辑);连劭名:《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华夏考古》1998年第4期。从东汉魏晋时期出土的解注瓶及镇墓文的文辞都可以看到人鬼异路、不相复注是丧葬仪式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表述形态。
(21)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22)王明:《太平经合校》,第293页。
(23)同上,第706页。
(24)刘玺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80页。
(25)道教仪式中所见的煞鬼疗疾技术都需要首先明确鬼的姓名,并根据其特点延请对应的官将与神灵。《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还可以看到鬼与疾病的对应列表。
(2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90年,第212页。
(27)CT1193:6a-8b;《道藏》,28:368。
(28)准确地说,这种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表述是将生活中对于疾病与灾厄的焦虑转化为可诠释和处理的叙述。由此,当生活中出现灾厄和疾病时,从诠释到处理的过程就可以在这一观念框架中展开了。简言之,从不确定的焦虑到可处理的危险,道教通过鬼的观念及其功用的描述解决了人鬼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将它指向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29)CT1193:8a-10a;《道藏》,28:368。
(30)CT1193:10a-10b;《道藏》,28:368。
(31)CT1193:18a-19b;《道藏》,28:370。
(32)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33)高丽杨点校《钟吕传道集西山群仙会真记》,中华书局,2015年,第52页。
(34)CT1016,13:7b-8a;《道藏》20:536。
(35)参见卢国龙、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177-206页。
(36)约出于东晋南期。原系《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之后半篇,后分出单行。底本出处:《正统遭藏》正一部。参校:敦煌P.2865号抄本(后半部分)。
(37)CT584,1:3a;《道藏》10: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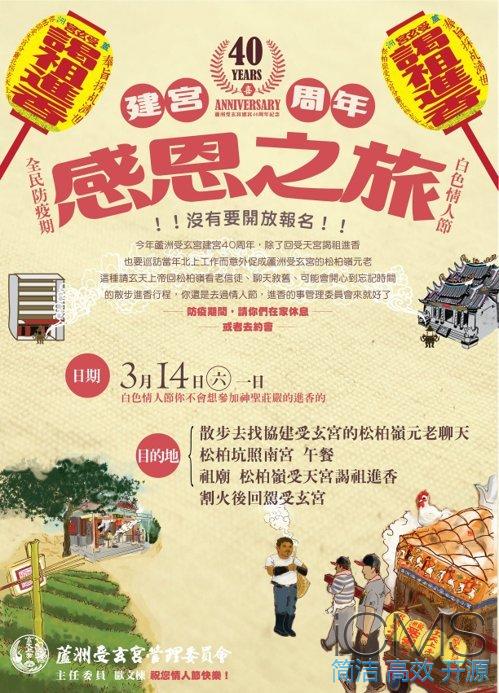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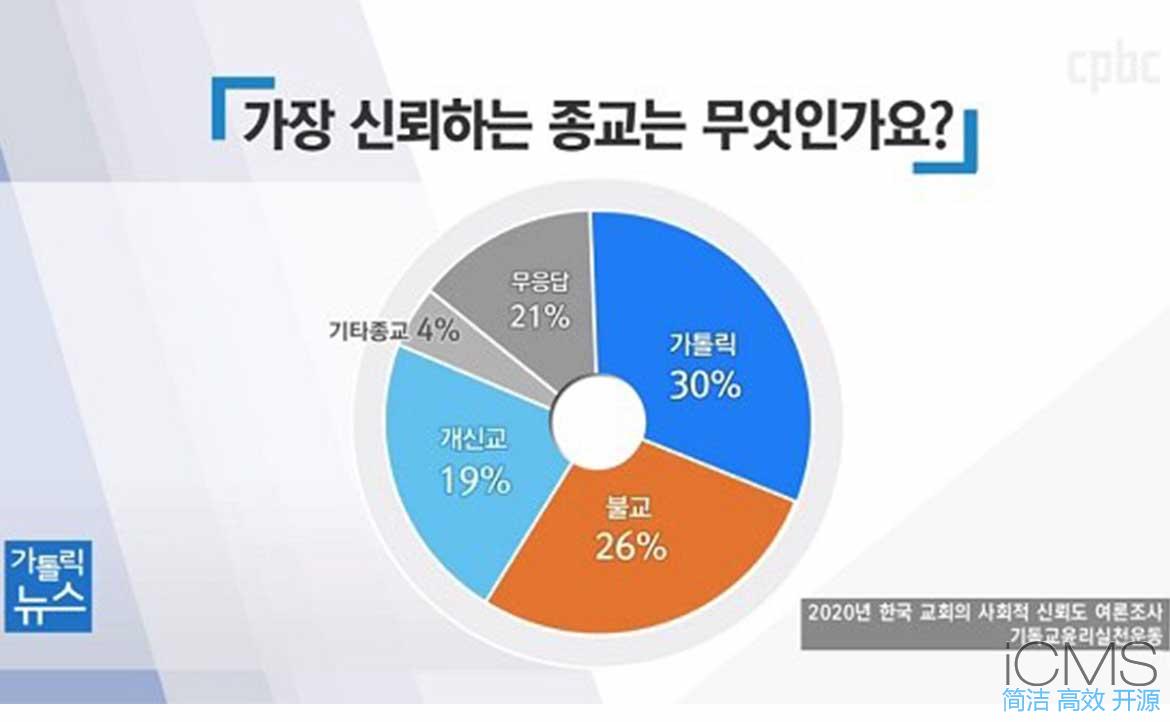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