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豫西民间诸神由正祀、淫祀以及私祀组成。推行正祀、禁毁淫祀、容忍私祀是明代国家关于民间信仰的指导方针。在明代豫西,地方官、理学家以及耆民成为推动民间信仰政策的三支社会力量。地方官的行政调控、理学家的道德声援以及当地耆民的在地化推动促成明代豫西民间信仰呈现两个鲜明特点,即正祀民间化加速以及儒释道交融性增强。透过明代地方官及理学家对豫西乡间信仰的引导、控制情况,可知这一时期主流统治秩序与社会传统、民间信仰间的互动规律。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研究硕果累累,却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与华北地区、华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等地研究成果相比,中原民间信仰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中关于豫西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则寥寥可数,且多集中在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关系、民间艺术与民间信仰关系、民间庙会与民间信仰关系等方面,缺乏对豫西民间信仰作整体论述以及深层分析。对此,本文拟作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豫西民间信仰体系
豫西区包括河南省西部的平顶山、洛阳、三门峡,北隔黄河与豫北区和山西省相望,西与陕西省相连,南接豫南区,东连豫中区。豫西地区在明代所对应的区域主要指河南府和汝州,其中河南府包括1州11个县,即陕州(含灵宝和阌县)、洛阳县、登封县、永宁县、渑池县、嵩县、偃师县、巩县、孟津县、宜阳县、新安县以及卢氏县,汝州包括4县,即鲁山县、宝丰县、伊阳县和郏县。就祠庙礼制而言,明代豫西民间信仰由部分正祀、私祀和淫祀组成。
(一)正祀
豫西正祀内容驳杂,大致可归三类:第一类,坛。此类主要包括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等。第二类,文庙贤祠。文庙贤祠在全国各地亦普遍存在,如二程夫子祠、曹学正祠等。二程夫子祠尽管遍布天下,洛阳却独有其专祠,正如顺治年间洛阳县令武攀龙《重修二程夫子祠堂记》提到,“天下之祀者各有其配殿,而洛阳之祀之者独有其专祠”。第三类,一些神庙寺观。坛壝和文庙贤祠显然不是民众崇拜的对象。明代豫西民众崇拜的正祀,集中在神庙寺观。据弘治《河南郡志》和正德《汝州志》所载,可窥明代豫西地区民间信仰正祀大致状况。
寺观是明代豫西地区正祀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据弘治《河南郡志》记载,河南府寺观为123寺,34观,3宫,2院,1庵,其中登封县名列首位,已达24寺。据正德《汝州志》记载,汝州寺观为69寺,14观,1堂,1院,其中汝州城名列首位,已达19寺。
(二)淫祀
先儒经典《礼记·曲礼下》将淫祠解释为“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就阶层意识而言,祀典对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所应拜祭的神灵,都作明晰规定,越级而祭,构成淫祀。譬如《曹端集》描述明初渑池县存在僭越之祭,悖于礼制的状况:“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祀数百,一村一落,神祀数十,家家事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与五岳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享一祀,悖礼伤教,不可胜言。”
就祭祀内容而言,礼制范围规定外的怪力乱神,都构成淫祀。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譬如登封县少姨庙,“少姨庙碑:《金石录》:少姨庙者,则《汉书·地里志》,嵩高少室之庙也。其神为妇人像者,则故老相传云启母,涂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涂山氏化为石而生启,其事不经,固已难信。今又以少姨为涂山氏之妹,庙而祀之,其为浅陋,尤其盖俚俗所立淫祀也。”少姨庙之所以被列入淫祀,由于“其事不经,固已难信”。郏县二郎庙庙祀兴盛,所祀对象为秦蜀郡守李冰之第二子,因无功于民,宗社不守,成为淫祀。
万历时期汝州艾先生曾谈及汝州淫祀之盛况,“诸庙祀多淫渎不经,有不可胜书者。今惟取其名义攸关与创自前代者,书之而已。”
(三)私祀
私祀指祀典与淫祠之外民间神灵的第三种状态。赵世瑜把私祀称为杂祀,并且指出正祀是必须崇拜的,杂祀是允许崇拜的,淫祀是不允许崇拜的豫西私祀与淫祀相比,许多相传于民有功;与正祀相比,这些祠庙又不明来历和依据。据《伊阳县志》载:“商山庙,汉四皓之一,在南街,建造未详何代。明万历癸丑邑民乔应科,叚守福,赵矢爵等重修。邑增生常淮撰碑记有云,普成男成女之化,司痘疹疮疫之疾,亦不详其何据也。谢志云,汉五忠庙,薄姬庙,商山庙皆古刹,其称薄姬与商山有功于伊,皆不经也。”薄姬庙与商山庙虽然相传有功于伊,有功于民,但是因其来历不明,所以难入正祀之列。再如宜阳县的噀酒龙王庙,明人李士登《重修金牙山噀酒龙王庙记》道出此信仰并非淫祀缘由:“公亦有庇于世道焉,是神也,庙也,非世所谓淫祠邪魅,无益于民生,无关于祸福。时遇亢旱,村落中居民或祷雨祈泽,有归家而雨者,有中途而雨者,如响之应声无不验。”就民众而言,唯灵是验是敬神祀神的根本所在,无所谓私祀和淫祀。民众经常为所奉神灵制造灵验事迹,使其“有功于民”而免淫祠之禁。
二明代豫西民间信仰及地方调控
地方官为政教立国,从行政层面推行正祀,禁毁淫祠;理学家为传承儒教,从思想层面推广正祀,排斥佛道。耆民作为豫西民众代表,或向地方官出示民意,建言献策,或组织民众,修庙建祠,成为沟通地方官和民众的中坚力量。
(一)地方官的行政调控
由上表可见,城隍庙数量居于诸庙之首。明人程兰《重修偃师县城隍庙记》提出重修城隍庙宇的动力,“我国朝自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为百神主,乃敕封天下城隍,郡曰灵祐侯,邑曰显应伯。诏所在郡邑立庙祀之”。豫西地方官除了修祠建庙,响应正祀,还树立“我与尔神均守土”的共治意识。明人王祎《渑池县王丞君驱虎歌》道出,“王侯承诏来作丞,民有疮痍手摩抚。下车走谒城隍庙,亲写文移对神语。为言幽显虽有分,我与尔神均守土。”地方官为“显”官,城隍神为“幽”官,“亲写文移对神语”表达王侯对城隍神的敬重,亦反映城隍神在明代豫西的社会影响力。
地方官员经常主持拜祭仪式,与神灵沟通,并向民众宣传灵验,以达到上宣德意,下亲斯民。正如许珀《汝州城隍感应记》记载:“通天下郡邑必有庙祀城隍者,以其捍灾御患使水旱寇攘不能干犯者,非神莫为之尸也。……宋侯以乡进士擢守是郡,几祷屡有感应之效。成化戊戌春旱麦不茁,民心忧惧,侯祷而即雨。夏复旱,侯□然于心,乃肃诚祷于庙以请雨,不日而甘澍大降。……由是四民歌谣于野,官吏胥庆于庭,皆曰神感。郡守之诚而其神亦因致应而益灵也地方官祈祷城隍庙并且获得灵验,从而宣传作为正祀的城隍庙的灵力。
制定乡约、发布告示与禁毁淫祀是明代豫西地方官推广正祀的重要举措。据弘治《河南郡志》记载:“如本府第一百户或七八十户分立一社,春秋专祀无土五谷之神,为春祈秋报。凡土俗淫祠,一切去之不祀。……有疾病医药不得师巫,假降邪神以乱正苑。丧从礼哭奠,僧道不得出入人家。作道场佛事,凡吉凶事皆有赠遗。”地方官将民众编为里社,以此为单位分派祭祀事务。乡约规定春秋专祀土谷之神,不得祀淫祠、信邪神、师巫等。隆庆陕州知州方扬教导当地民众节财正俗,不许信惑异端:
陕州为禁约事,照得该州迎春一节。国有正典,费有常经,似不可缺,但礼主于简……除巳行照例迎春,合用春牛芝、神花鞭、金鼓不禁外,其一切儿戏繁文尽行革去,仍俦示仰在城在乡居民知悉。自令各守尔分,各省尔财。敢有仍前纵肆张乐、携妓、搬剧、赛神及一应信惑异端,烧香拜佛布施者,许诸人报官拿究,仍各枷号示众,决不轻贷,须至告示者。
这篇告示极具威力,不以劝说讲解的口吻,而直接“许诸人报官拿究,仍各枷号示众,决不轻贷”,可见此现象的普及程度。除了运用乡约告示外,地方官亦通过禁毁淫祀来教化民俗。如:“(郏县)曹豹,江南华亭人,进士。洪治间知郏县,持身端节,政多循良,修订县志,毁淫寺,为崇正书院。”“(伊阳县)隆庆辛未,邑侯武公下车谒庙……即以兴做为己任,节羡余,雇工役,毁淫祀。”等等。
明代豫西地方官围绕“推正祀、禁淫祀”,通过修祠建庙,树立与神共治意识,主持拜祭神灵仪式,发布乡约告示等方式向民间社会宣传正祀,落实政教立国方针。
(二)理学家的道德声援
明代豫西理学人文荟萃,既有被推为明初理学之冠的曹端,又有阎禹锡、王尚絅、尤时熙、陈麟、孟化鲤、王以悟、张信民、吕维祺等知名理学家。这些理学家对于“推正祀、禁淫祀”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理学家从思想上排斥佛道,“阴阳二气聚时生,到底阴阳散时死。生死阴阳聚散为,古今造化只一次……空家不解死生由,妄说轮回乱大猷”。
其次,理学家身体力行,不用佛事,化民成俗,譬如新安县理学家孟化鲤和吕维祺不用浮屠事,教化乡民:“丧礼,韩佟志云,丧用浮屠,理学二先生不用,间或化之,谓孟云浦、吕忠节也。按,新士民多不用佛事,其不饮酒、不食肉、不听乐、不庆贺,虽未能如古人之严然,犹不至荡闭败度,公然肆行。”
再次,理学家坚决抵制巫术迷信和淫祀。陈麟认为,“作乐娱尸为凶丧陋俗,断而去之在王以悟的侄子王尔恕死后5年,其子王伯贞也相继死去。王尔恕的弟弟王尔慈在巽峰上建一祷祠,以求平安,并请求其叔王以悟撰碑文,部分碑文如下:“岂祷以理不以神,以身不以文,以平日不以一时耶?占丈君者澡身浴德,孝弟为先,忠信为本。一切机械变诈,欺天罔人,誓自今舍旧图新,无人非,无鬼责。心安德滋,精和神固。何患乎无嗣。”王以悟继承了儒家不信鬼神的传统,并且教育后辈“以理不以神”,切实履行儒家“孝弟为先,忠信为本”的主张。
理学家曹端坚持信理不信巫,并且以理羞辱巫觋,打击巫蛊之说。在祠神信仰方面,他也极为严厉,其曰:“时渑淫祠过多,先生上书请毁之。邑令杨某者,从其言,即令先生躬诣四乡,监毁百余所,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焉,惟存夏禹、雷公二庙而已。”
最后,明代中后期理学家逐渐放宽对异端的排斥,将儒教伦理纳入民间佛道信仰中。譬如张信民亲自撰写《玄帝庙碑记》:“按《玄帝经》:净乐国王太子得元君授道,修行显化,白日登天,此其说之妄,皆后世好事者为之,不足深辩。考之《易》曰:帝‘劳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然则玄帝者,水帝也。……窃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为之智。水发万物,智干万事。故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而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明圣之由于智也。无智,则仁流于兼爱;义流于为我;礼流于奢靡,而谓忠信之薄……”张信民将儒家伦理与玄帝由来结合起来,从而将道教神明儒教化。
(三)耆民的推动
明代豫西地方官大多并非本地人,对当地信仰状况并不熟悉。耆民作为当地社会精英为其出谋划策。豫西耆民请求地方官为灵验神灵请祠建庙。黄良弼任正德年间汝州学正,作《风伯庙记》:“有耆民尚满、林兴等长跪而请曰‘吾等官庄保民也。地故有风伯庙,神最灵,祸福于人者最速。前此莅吾民者,率以秦越,视祀事弗修。神震怒,数暴风偃禾杀稼,岁十无一稔吾保,害辄先之。自吾张公至,轸念元元,索其神而祝焉,且祀曰:若能岁福吾民,当举庙貌一新之于□。’”“祀事弗修”导致“神震怒”、“偃禾杀稼,岁十无一稔”,耆民以自己亲身经历来体证神庙的灵验。耆民除了向地方官表示民意,出谋划策外,他们亦经常组织乡里,共同修建祠庙,如嘉靖四年(1525)巩县赵迎《重修五岳庙记》所载:
耆老耿彪、李玄等言曰,庙之创建久矣。吾乡世谨其祀,每获感应之庇。昔寇贼扰境,乡先生费府率里中子弟而御之,神显法像于营阵之表,遂使贼虏褫魄而退。时亢旱殊甚,虔祷方兴,霖雨辄施,岁赖以稔。顾其久而庙貌颓圮,费公乃倡我辈,慨然而言曰:“神为吾乡之庇也,久矣!不知其报,可乎?而坐视其颓圮,可乎?”且曰:“选材木以修葺之,固也。”
此外,富有耆民常常捐资建庙,支持正祀,“城隍庙在县治南街,嘉靖七年,乡民张良臣、李裴改修。三十二年,李节乐因庙檐前空露,自捐己财,重建卷棚”。
三明代豫西民间信仰特征
在地方官和理学家的调控下,明代豫西民间信仰呈现一定的社会特征。就礼制层面而言,正祀的民间化进一步加速。就思想层面而言,儒释道互融性增强,民间神明儒教化加速。
(一)正祀民间化
明代豫西地方官通过建置祠庙、主持拜祭、讲述灵验等方式确实提高了正祀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祀典中的许多神灵,逐渐被豫西民众吸纳,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许多正祀都成为明代豫西民间供奉的对象。譬如城隍庙、三官庙以及东岳庙等。以陕县山口村三官庙现存洪武年间两块碑文为例:第一块,“夫人之所以葆享富厚,举之福而□罹刑……天地水府之神主宰于□,赐之福而赦解其罪。”第二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作善降之百祥……公讳江者乃于嘉靖丁酉春,鸠乡之善士刘洗、刘□……适有刘花、刘儒、刘昌□村中隙地一段……以为诸善士倡,由是,乡之善士或输以资或助以力。”官方宗教的目的在求国家社会的福祉,民间信仰则多半为了民众自己一己的利益,因此民间信仰与官方宗教的差别也许不在其根本的宇宙观,而在于它们各自所关心的问题。灵验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利益结合点,亦是正祀民间化的前提。譬如明嘉靖时期灵宝人许赞《重修东岳庙行祠记》描述阌乡民众对东岳庙的崇拜在于“有祷辄应”。
第二,正祀与私祀之间并非不可逾越,许多正祀来自民间。如陕州“白龙庙,州东百里旱,祷郎雨。万历间敕封都龙神。一在原店村。”个别民众因特殊灵力,亦会受地方官员邀请,参与官方拜祭。如刘真还“万历间修真长春观,炼五雷正法,驱雷鞭电,唤雨呼风,无不正应。每旱郡守必请祷雨,寿一百一十岁,无疾而化,今炼将台犹存。”
第三,明中期以来,频繁的朝山进香活动推动正祀神灵的民间化进程。譬如河南府孟津县小寨村所存明嘉靖二十年(1541)《创建祖师庙碑记》:“盖祖师者,为天下之镇,乃生民之所仰慕者也。温秀等仰神功之浩大,联众心之精白,于嘉靖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谋于乡众,萃铜肖像,欲敬送于武当山。乡众曰:‘神无往而不在,与其送于武当山而阻山川,孰若建一祠而朝夕奉事乎?’”前往武当进香,成为当时豫西民间盛事。这样的进香活动耗时耗力,为方便起见,一些民众便倡议于本地建祠供奉。
(二)儒释道交融性增强
地藏信仰是民众在佛教基础上吸收儒教而成,在豫西地区普遍流行,譬如宝丰县“地藏王监斋二殿,主持僧性海于隆庆二年冬月谋社首马驰等二殿”,“观音地藏祖师三殿并钟楼,始于正德十四年,落成于嘉靖元年”。道家与佛教因果轮回、儒教伦理纲常相融,向民间社会渗透。譬如陕县山口三官庙,在天官紫微、地官清虚、水官洞阴三帝前方的殿内顶梁大柱上雕塑两条巨龙,利爪分别抓一人头,据说这是戏剧《清风亭》中张继宝忤逆不孝、忘恩负义、激怒上苍的可耻下场。
明代豫西民间神灵崇拜饱含极强的伦理化色彩。譬如明人宜阳县人顾达在《谒女几祠》一文,讲述了关于女几祠庙主彭娥的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宜阳城西九十里,一山魏然名女几。上有窈窕之神祠,服靓粧淡淡如洗。其说昔当永嘉时,彭娥促此逃乱离。偶因出汲此山下,道逢群寇将污之。娥因愤呼向天号,宁死义不受其辱。奔腾忽得迓山阳,以首便效其共触。皇天赫怒山为摧,崖石中分如凿开。娥既脱身趋以入,山即复合真怪哉。如何强奴未解理,犹自逐之势不已。跳踉踯躅知几人,一一投身甘磔死。当时汲器真有灵,化为巨石犹像形。至今樵客或时见,欲往从之应未能。我来观风持宪节,几度经过曾造谒。慨想高风不可追,为作长歌颂贞烈。
由上可知,女几祠在宜阳县受到供奉与彭娥所传递的贞节精神分不开。这种精神符合传统伦理道德,因而受到宣扬。
明代豫西地方官和理学家通过宣传符合传统礼教的庙祀,将儒教伦理灌输到民间信仰中,致使民间诸神的儒释道交融性增强。明代豫西乡间诸神在传统的庇佑护福功能外,还承担起教化民众、睦邻乡亲等其他功能。这种以神圣功能为主,向神圣与世俗功能并重的转变,离不开地方官的宣传、理学家的化民成俗以及豫西民众的融会贯通。
四结语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豫西,地方信仰活动既担任地方自主性的枢纽,又承担国家统治意识形态的媒介管道。本文将豫西官吏的行政调控和理学家的思想调控区别对待,进一步分析两条渠道对正统意识的运输方法和输送能力。
明代豫西地方官以禁毁淫祠为主,清代以严惩邪教为主。这传达官方对民间信仰管理方针的转变,即以预防为主转为以惩罚为主。明初理学家在获得“统治思想”的桂冠之后,极力排斥佛道。到了明中后期,伴随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一批理学家改变排斥佛道的态度,开始利用民间神灵推动神明儒教化。这是理学家面对民间信仰盛况作出的妥协。
在地方官和理学家的调控下,正祀的民间化进程加速,儒释道进一步融合。耆民成为重要的地方推动力量,不但利用个人财力助修地方神庙,而且发挥地方号召力共修民间庙寺。此外,豫西耆民还积极向地方官建言献策,呈报民意,使明代豫西民间神庙在彰显正统性之余,尽显地方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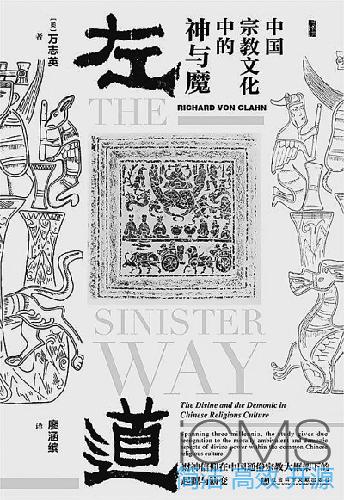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