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虎
中山大学哲学系;
儒学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互动, 且这种互动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整个文化各要素之间在文化内部进行整合的动态过程。儒学“独尊”以后, 儒学以毛细管的作用力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民间信仰亦受其影响。民间信仰将儒学发展为思想内核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信仰支撑, 两者融合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宗教形态。儒学与民间之间能够互动, 本质上还是源于两者皆附有的宗教性特征, 两者虽都不是体制上的宗教, 却一直发挥着宗教的影响力和作用, 并融会构建神学政治文化生态。
儒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创立的学术体系, 民间信仰则是普通民众对鬼神崇拜的观念整合, 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儒学与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 两者之间存在互动, 且这个互动应是一个双向融会的动态过程。儒学下移, 民间信仰亦存在寻求理论支撑的“上升”, 由此而形成碰撞, 碰触点应是两者皆附有的宗教性。因此, 若论及儒学对民间信仰理论的构造, 谈两者的内在互动, 实际也是在梳理儒学与民间信仰宗教思维存在的问题, 以及这种宗教性所构建的整个神学政治文化生态。
一、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
儒、释、道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教”, 对儒教是否宗教尽管存在着巨大争议, 但三者并列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事实。按照吕大吉等人对宗教的定义与认识, 中国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形成之前没有“宗教”存在。然而, 没有宗教, 不代表没有宗教观念, 没有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性的文化形态。吕大吉也说“原始人的宗教, 不但是整个人类宗教的发端, 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的源泉。”[1]长期以来, 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崇拜, 比如原始宗教信仰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 中国人对自然天神、地祇诸神、人鬼祖宗等诸多的神明都是极度迷信的。这些“宗教”看似不发达, 却又有无处不在的种种信仰, 到处弥漫着神秘主义和神本色彩。
两汉之际, 佛陀东来, 且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魏书》载:“及开西域, 遣张骞使大夏还, 传其旁有身毒国, 一名天竺, 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2年) , 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此后的东汉初期, 光武帝之子刘英, “少时好游侠, 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 学为浮屠斋戒祭祀”[3]。这些正史中有关佛教流传的记载, 给人一种自上而下传播的假象, 至少是值得质疑的。这是因为:其一, 正史一般均采自官方资料, 多要依靠政府文献的支撑, 而王公贵胄接触佛教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百姓, 尤其是帝王对佛教的信仰更为惹人关注, 如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而寻访高僧建白马寺, 成为最早寺院的记载, 所谓“最早”其实也有争议;其二, 佛教为了扩大影响, 克服水土不服, 故有意识地接触政治权力中枢, 并希望得到官方认可, 因而佛教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接触的都是当地政府;其三, 佛教东来之际, 正值东汉社会动荡之时, 一些民众饥寒交迫, 食不果腹, 佛教时不时地会被一些地方军阀割据利用, 使其成为民间宗教的理论武器。如《后汉书》载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 本被刺史陶谦委派去运粮, 却中途造反, “大起浮屠寺”[4], 继而成为汉末投机军阀。社会动荡, 国家政权风雨飘摇, 儒家学而不教, 民间宗教野蛮生长, 佛教轮回之说满足了底层百姓的信仰诉求, 因而容易被民众接受, 并与民间信仰混杂其间成为民间宗教的理论旗帜。佛教传入形式上看是由上层社会逐渐推而广之才延伸至下层百姓, 事实上信仰的扩散却与社会阶层关系不大, 而是一个遍地开花的过程, 佛教的深入与传承靠的是诸多苦行僧在民间修行与布道, 利用民间信仰力量推进的结果。
佛教在社会底层的传播, 在客观上为道教发展提供了借鉴, 利用佛教成教模式, 道教得以脱胎成教。道教是在中国本土形成的宗教,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期道教, 或称之为“原始道教”, 在中国文化大环境中不断激荡, 从氏族社会一直延续到汉末, 逐渐在鬼神崇拜、神仙信仰和黄老学说的基础上, 融合民间宗教的形式而发展起来, 虽受儒家讥讽“杂而多端”[5], 然实质上与汉代“新儒学”的形成颇为相似。道教的真正定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两汉开始, 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称得上确立。东汉末期, 道教派别林立, 道士各持己见, 其中符箓派凭借治病救人, 扶弱助困, 因而得到了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加之东汉末期混乱的社会背景,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顺势而起, 张角、张修、张鲁等人才能崭露头角, 把道教推向真正的宗教之路。在汉代道教形成的过程中, 民间信仰如影随形, 在一定程度上从底层社会为道教的定型起到了推动作用。道教借力民间信仰的发展与佛教并无二致, 且道教对民间信仰吸收更透彻。伴随着道教的逐渐成熟, 才慢慢脱离民间信仰文化模式而独立发展, 但至少在汉代, 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佛教能够独尊, 能够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相反, 佛教的传播延续了民间信仰的形式, 是面向社会各阶层全面铺开的制度性宗教。与此同时, 道教利用民间信仰, 以民间宗教的形式, 以道家思想为理论逐渐铸造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与佛教、道教相比, 民间信仰虽不是宗教, 却又类似宗教, 丁毅华称之为“类宗教”,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泛神论的、以我为中心的、功利性的、严肃和戏谑同在的“类宗教”, 又是始终存在的, 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有重要地位。[6]这至少表明, 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存在内在的一些结点或共通之处。谢扶雅在谈论宗教哲学问题时指出, 中国最初文献上所现之宗教, 亦当由先史时代之宗教动作如庶物崇拜、法术、符象等群众性宗教, 进化而来者也。[7]成熟的宗教形态是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发展的过程, 民间信仰只不过是宗教发展进程中的胚胎, 带有更多的原始性, 一直孕育在文化母体内。
儒学从汉代“独尊”以后, 其发展路线呈现多元趋势。因为儒学本身的包容性和极强的兼容能力, 故而也对宗教形态进行了一系列吸纳, 只是由于儒学在汉代代表的是官方意识形态, 因而看似没有与佛、道一样借力民间信仰。事实上, 无论是在儒学独尊之前还是之后, 都浸染于民间信仰。独尊之前, 儒学根植于神本社会, 萌发于天人信仰之间。独尊之后, 儒学熔炼百家而铸“新儒”, 儒学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汉代末期, 虽然儒学式微, 但仍主导社会主流思潮, 自上而下对社会文化构成影响, 这与佛的平面扩散与道的自下而上传播路线存在差异。在这种文化思潮激荡的社会背景下, 儒释道三教混杂, 无形中把力量的胶着点放在了民间信仰的争夺上。因此, 民间信仰集中体现了这种社会复杂的精神现状和文化思潮交汇的景象。也可以说, 在中国文化的大熔炉里, 民间信仰并不纯粹, 它是熔炼和吸附了中国多种文化内涵的民间的人文信仰。有人说, “民间信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宗教形态, 是在各民族群众广泛流行的、具有明显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8]。与其说中国社会信仰是儒释道三教并立, 不如说是儒释道与民间信仰等信仰的多元共存。正是如此, 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信仰文化, 在外国人看来“每一个中国人在伦理和公众生活上是儒家, 在个人生活和健康上是道家, 而在死亡的时候是佛家, 一路上还加入了一些健康的萨满教的民间宗教”[9]。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人文”宗教形态, 是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宗教”模式共同作用, 互相影响、吸收、交融的产物。
二、儒学下移:构建民间信仰的思想内核
儒学与民间信仰之间虽不能绝对地画上等号, 但儒学能否作为民间信仰的内容或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却不是一个伪命题。分析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两者共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 是文化生态链的有机构成;另一个是两者的融会力是否存在, 即儒学自身是否能够融入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否有容纳儒学的可能。
(一) 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渊源深厚
若从神学政治文化体系看, 儒学与民间信仰之间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互动问题, 两者相濡以沫是不争的事实。儒家文化以儒学理论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儒学与民间信仰的渊源关系就源于且共生于中国文化的大文化生态圈, 渊源颇深。其一, 从信仰理论层面看, 儒家是有信仰的, 有神祇观念, 且这种观念有确凿的儒学理论支撑。比如说到对鬼神的态度, 《礼记》曰:“夏道尊命, 事鬼敬神而远之,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10]无论是敬神还是远离神, 起码没有脱离对神这个存在的认识。又比如一些民间神祇常常被儒家引用, 说到灶神, 《论语》曰:“与其媚于奥, 宁媚于灶。” (《八佾》) 说到五福神, 《尚书·洪范》曰:“五福, 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11]还有一些民间神祇, 儒家给予过解释, 如寿星神, 《尔雅·释天》曰:“寿星, 角亢也。”[12]《通典·礼四》曰:“晋以仲秋月, 祀于国都远郊老人星庙。季秋祀心星于南郊坛心星庙。东晋以来配饗南郊, 不复特立。”[13]西王母娘娘神早出自《尔雅·释地》, 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 谓之四荒”[14], 而后逐步演化为民间信仰神祇。从儒家经典诸多论述中, 大体可以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不迷信鬼神的, 但却不得不面对反复地对神的态度解释的困扰。至少表明, 儒家思想难以脱离中国文化滥觞于鬼神的客观事实。其二, 从社会实践上而言, 儒家对民间神祇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初道家本宣扬求仙之术, 武帝时仍痴迷巫鬼, 王莽借术士之学而篡汉, 光武帝依旧以谶纬复兴汉室, 儒生焉何独善其身?东汉王充一味否认鬼神存在, 却忽略了整个社会对鬼神的情感归属, 割裂了鬼神观, 反倒成为一种早熟的社会信仰而不合时宜。王符倒是极为中庸, 与其说出真话, 别人不相信, 不如顺着群众能够接受的思路, 讲出道理, 把人们引导到正道上来。[15]因此, 王符主张与鬼神交通, 试图顺势而为, 倡导“鬼神与人殊气异务”[16], 力求神道设教。儒学与鬼神信仰之间有着理不清的种种瓜葛, 使得儒学成了民间信仰传播的重要推手。
那么, 在儒学与民间信仰相互影响的过程中, 各自都扮演什么角色呢?作为儒学, 在汉武帝以后的专制政权统治社会下, 一直占居着思想的统治地位。大量的知识分子都以儒学为主要知识基础, 并对其学习、发展、改造和利用。然而, 事实上, 只有少数的儒生能跻身统治阶层, 大部分知识分子只能长期在民间生活。但他们所具备的儒学思想根基没有改变, 乃至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信仰, 乃至思维方式。宋代以后, 社会分化加剧, 儒学下移的速度和广度史无前例。明朝叶向高儒学修养精湛, 且又是民间信仰的积极参与者, “富贵无心想, 功名两不成”正是其流传民间的真实写照。[17]清代儒生蒲松龄考取功名无望, 弃儒从商却又以儒会鬼神, 谈鬼说魅之间, 实际上早已把儒学融入民间信仰。清人纪昀人在朝廷心在民间, 亦是喜好鬼神, 把儒家说教完全渗透于鬼神精怪言语之间, 其作品《阅微草堂笔记》可谓是儒学与民间信仰的绝好见证。可以说, 儒学就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最重要的思想内核。
民间信仰, 又称为“民俗信仰”或“信仰民俗”, 说明民间信仰与民俗信仰并无实质区别。既然能被称之为民俗的信仰, 或信仰的民俗, 自然是兼具了民俗与信仰两者的功能和特征, 由于信仰往往涉及的是宗教问题, 因而, 民间信仰就是民俗中的信仰活动, 或信仰活动中的民俗部分, 就是民间的准宗教, 即“民俗宗教”。儒学的下移, 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下移为民俗, 构成民间生活的一部分。从中国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看,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儒学与民间信仰之间的渊源是深厚的, 长期的。
(二) 天人哲学的回归:沦为民间信仰的儒学
儒家“纡尊降贵”成为民间信仰是否可能呢?方旭东认为是不可能的。儒家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专职传教人员, 更要命的是, 儒家甚至没有一个鲜明的教义, 其中包括民间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祇、彼岸许诺。说到底, 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从而对后者也无法构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胁。事实上, 在中国古代, 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仪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灾, 在晚明甚至出现很多像徐光启那样自愿受洗的儒者。作为民间信仰, 儒家不愿亦不能, 这诚然是儒家在当代的悲剧, 人声喧哗的曲阜教堂事件无法扭转这种悲剧, 只不过将这种悲剧放大了。[18]从民间信仰和儒学之间的互动看, 至少在汉代, 两者之间就存在关联, 儒家思想沦为民间信仰成为可能。辛亥革命以后, 儒学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 儒学的全面下移, 本身就是民间信仰内核的儒学更是民间色彩浓重, 这点在当代的中国台湾社会更为凸显。
儒学本身具有的包容性 (兼容性) 是儒学能够与民间信仰互动的前提。李锦全就认为儒学本身具有包容性, 这种包容既有中国文化内部之间的包容, 也有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他说:“我们对孔子以来儒学思想的包容性是应该给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长期不断丰富和发展, 儒学的包容性是功不可没的。”[19]这种包容性是儒学与生俱来的, 从孔子开始就已经具备, 到了汉代又得以全面体现。杜维明说:“汉代儒学的显著特征便是兼容并蓄, 它象征着一种颇用心思的努力:把看起来彼此排斥的观念系统熔铸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观之中, 董仲舒的人文宇宙论就调和了多种学说。”[20]董仲舒提倡的儒学, 不是孔子那个时代的原始儒学, 而是熔炼百家思想的新儒学。同时, 不容置喙, 汉代儒学也是糅合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信仰和汉代民间信仰的“新儒学”。也正是因为儒学的包容性, 让儒学呈现多面性, 以至于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发展方向。
儒学化民成俗, 深入民间。儒学民间化是儒学与民间信仰互动的必然路径, 也是必然结果。只有让儒学走进民间, 才能让民间信仰接纳和融合儒学。近年来兴起的乡村儒学、书院、国学热, 基本上都是儒学民间化的表现。民间儒学, 成为重构乡村精神世界的核心。2016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学术研讨会, 钱逊、王殿卿、张践、李存山、颜炳罡等人就提出了乡村儒学的重要性, 钱逊认为儒学复兴不仅包括高端学术研究, 也包括在民间的传承发扬, 后者是儒学的根本和基础。[21]儒学的民间化让儒学下移民间, 把儒家文化以一种非官方的形式在民间给予传播, 这是继续传播儒家文化传统的必然。儒学下移, 儒学进入民间, 儒家倡导的价值观与信仰必然与民间信仰发生碰触, 要么改造要么适应, 儒学与民间信仰的贴近, 是天人哲学的一种回归而非儒学的沉沦。当然, 儒学的民间化之路并不是构成儒学与民间信仰互动的全部因素, 但也不失为儒学是在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从民间信仰角度说, 民间信仰自身有着能够吸收儒学的重要基因。刘永华从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提出的“存在一个中国的宗教系统”的观点出发, 认为民间信仰就是一个“复数”, 而非“单数”[22]。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宗教系统中, 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民间宗教神祇众多, 在中国这样一个看似无宗教的社会体系里, 却又是人人信教, 人人拜神。自古而今, 中国各地大小庙宇延绵不绝,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神祇被供奉。小到一个家有祖先神, 大到一个国家有天神和社稷神, 社会上各行各业又有自己的行业神, 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没有哪个没被纳入民间信仰神祇的系统。可以说, 中国的神祇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二是神祇虽多, 却又不成体系, 神与神之间没有姻亲关系, 神与人的沟通又非常简单, 极其零散、随意。民间信仰的系统没有什么稳定性, 今天是鬼, 明天可能就被奉为神;这里的神香火鼎盛, 在那里可能无人知晓;同一个神祇, 这里一个样子, 那里又是一个形象。相对于儒家文化的熔炼百家, 有一些相似之处, 只是民间信仰吸附力极强却又系统性差。三是民间信仰禁而不绝, 死而不僵。民间信仰虽然是民众自发的情感表达, 但极易受人为操控。特别是对于有碍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律, 有害于公共道德和安全, 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民间信仰, 政府是反对的, 甚至严格取缔。但历经千年, 这种信仰却依然存在, 生命顽强, 可见在民间还有存在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民间信仰与儒学能够互融与共存, 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儒学与民间信仰的这种互相融会的现象, 本文暂且称之为“儒化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儒教”。从民间信仰角度说, 儒学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实际上是一个儒家思想渗透其中的动态的“儒学化”的过程, 所以称之为“儒化的民间信仰”并不为过;从儒学角度说, 儒学作为儒家思想体系, 不断吸收民间信仰这种“弥散型”宗教, 这与任继愈等人提出的儒学自身的宗教化过程的“儒教”还是有差别的, 是吸收了民间信仰这种“准宗教”的儒学, 是民间信仰化的儒学, 与“官方儒教”相对, 是“民间儒教”。这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 都是儒学与民间信仰会通的概括。需要指出的是, 牟钟鉴等人并不赞同这种“儒”与“民”的会通。牟钟鉴认为, 在中国宗教史上, 存在着官方信仰、学者信仰与民间信仰相脱节的现象。[23]
三、宗教性:儒学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基因
关于儒学宗教性, 其实就是一个中西宗教观的碰撞产物, 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尤其是新儒家将儒学带向世界时凸显的一个儒学自身定位问题。大致来看, 唐君毅把儒学定义为“人文宗教”。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序言中说:“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 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 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 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 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24]2-6其实, 唐君毅想阐明的观点就是在中国“人文即宗教”。是否可以理解为儒学的宗教性其实就来自于人文, 源于中国文化内部儒学与“非儒学”之间的碰撞。正是因为儒学所具有的宗教性, 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儒教”, “儒学”即“儒教”, 是宗教之“教”。
在宗教观念上, 儒学有天人观为核心的天人信仰。天人观把儒学从“内在”导向了“外在”, 从“人”的关注上升到“天”的认识, 试图由“此岸”走向“彼岸”。一方面, 董仲舒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 一方面又不断地强调天的至高无上。从林存光对董仲舒提倡的天人哲学看, 他注意到了“天的宗教”和“上帝的宗教”之间的差别:“上帝的宗教”主要向人宣谕彼岸世界的福音, 使人们能够得到精神的救赎;而“天的宗教”所关注的则是此岸世界的政治统治问题, 是在天人关系的模式和框架下来肯定和确认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的权力和身份地位的以天命、天意为先验基础的合理性。[25]说到底, 天人关系既有哲学的一面, 又有宗教的一面, 只是董仲舒的天人哲学更趋于寻找两者对立中的一致性, 而张载的“天人合一”更多受到佛教思维影响更凸显儒学宗教特质。
“宗教”之所以为宗教, 是因为存在一定的宗教衡量标准。为什么道教是宗教, 而儒学就不是?李零说:“在中国, ‘天人合一’代表的是‘民神杂糅’的巫术传统, 道教也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宗教。这些可以算‘连续性’, 但‘绝地天通’之后的史官文化和民间巫木, 汉以来的儒与释、道并不是一种东西, 从总体结构上讲, 反而不如说是一种破裂。”[26]儒学之所以不是宗教, 无非就是它的理性主义占主导, 但不可否认它理性主义的不彻底, 它带有宗教性。大多数学者把儒学宗教性归结于儒学自身, 这并不一定准确, 儒学的宗教性其实更多源于外部借鉴, 尤其是对民间信仰这种弥散宗教的吸纳。
天人观因此而带有双重性, 既是儒家对先秦以来兴起的理性主义的坚持, 又是儒家试图把儒学建立为准宗教的理论尝试。天人哲学与信仰的确立无形中成了儒学新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儒学、儒教、儒术、儒巫从儒中分化出来。长期以来, 儒术占居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直到帝制逐渐解体, 儒教才成为大家关注的发展方向。当儒学在面对西方式宗教形态的时候, 这种“教”的差异和困惑才由此而来。实际上, 天人关系是哲学与信仰的统一体, 是理性与感性的交汇点。天人即是人, 即是天, 即是“一”。唐君毅在谈到中国宗教精神时说:“人精神之不朽而成为鬼神也, 其鬼神非只居天上, 而实常顾念人间。……吾之一切行为, 以至一切意念皆即形下而形上, 才通过主观, 即化为客观, 才属于我, 即属于天, 才自我所创生而辟发, 即为我所恭敬以奉持。则我于我之一切行为意念, 亦可敬之如天, 而自处如地。”[24]342中国宗教精神的实质, 就是对天人的敬畏, 是天我的一体。天人关系超越了信仰与哲学, 或者说儒学宗教观也只是天人关系之一维。因此, 单纯地讨论儒教问题, 其实应该从低一格的“天”观念看, 这个“天”恰好下移在了民间信仰这个层面, 儒教的宗教性也就显现出来。
从宗教情感上, 儒学有着丰富的“仁学”思想, 亦称为“人学”, 是重视人类情感的学问。儒家高举人性大旗, 正如柏拉图所说:“人的本性就像一篇困难的文章, 其意义必须靠哲学来译解。”[27]儒学本身就是一门伦理哲学, 生活哲学, 有着丰富的宗教情怀和情感。谢扶雅说:“动作兴奋情感, 情感流露神话, 神话复鼓舞情感及动作。”[7]儒家祭祀与神话就是儒学宗教情感的表达和凸显。这种情感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哲学。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家心性, 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孔孟之人学思想的发扬。唐君毅说:“孔孟思想, 进于古代宗教者, 不在其不信天, 而惟在其知人之仁心仁性, 即天心天道之直接之显示, 由是而重在立人道, 盖立人道即所以见天道。”[24]326在新儒家看来, 宗教情感就是靠心性来维系的。
古代祭祀虽不是一种独立的宗教模式, 却是一种宗教行为。唐君毅认为, 祭祀是儒学宗教性的重要体现。如他把儒家“三祭”看作是宗教性的一种重要体现:“祭祀时, 吾所求者, 乃吾之生命精神之伸展, 以达于超现实之已逝世的祖宗圣贤, 及整个之天地, 而顺承、尊戴祖宗圣贤及天地之德。”祭祀就是“使天地与人, 交感相通, 而圆满天人之关系”, 是天人一体神学政治的表达之路径, 所谓“三祭”, “含有今人所说宗教之意义”[28]。祭祀天地、祖宗、圣贤无不体现了儒学的宗教性。在当代儒教活动中, 祭祀常常被作为民俗活动看待, 体现的是民间信仰特征。儒学天人观的下移, 与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 宗教性恰好释放出来。
在宗教体制上, 儒学依附政治, 以儒家天人之学为理论基石, 建立了神学政治。汉代儒学分化出来的“宗教”其实是把儒学推到了官方宗教的地位, 构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国家宗教”。一方面这种宗教体制是为政治服务, 带有很强的国家政权性质, 是政治形成的产物。另一方面, 对儒学来说, 借助国家政治体制而构建的神学政治不也是一种儒家制度或体制吗?儒学在进入国家体制时带有很强的神学性, 这种宗教性既是政治的, 也是儒家的, 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体制。这种“国教”带有深深的儒学烙印和民族文化特征, 直至在海外形成了所谓的“中华教” (Chinese Religion) 。
在教主与神职人员上, 则由皇帝与儒生来填补。有人认为, 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 较有代表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解释是, 中国人早已有自己的国教, 这就是儒教, 孔子或皇帝就是教主, 这种观点以董仲舒、康有为和黑格尔为代表;另一种解释是, 中国哲学和文化主要是一种伦理实在论系统, 缺乏超越性, 因此宗教无法在中国生根, 这种观点普遍见于近代西方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29]其实, 皇帝和儒生在不同的场景中其角色和定位是不同的, 在政治权力构架中, 两者是君臣关系;在信仰层面, 即包含了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社会信仰中, 两者可以理解为教主与神职的关系;在儒学教育体系中, 两者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儒学的宗教性, 是与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相适应的, 即使宗教体制完备的道教, 其神祇也是杂而无序, 特别是在形成初期, 都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在长期的政治历史发展中, 儒学基本上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主流, 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生活的思想支柱, 两者亦步亦趋、形影相随。也正是儒学的包容、多面、松散, 长期以来以道德作为终极理念, 并牺牲自主性而依附意识形态, 相对于制度化宗教就缺乏统一的信仰、教义、组织、神职人员。大多数人 (如利玛窦) 认为儒教不是宗教, 是因为它不够纯洁, 什么都拜, 什么都信。所以有人就认为儒教信仰的是天地君亲师, 其中的天神崇拜与祖宗崇拜为核心, 对超验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希圣希贤) 为终极目标, 是宗教信仰体系。[30]这一信仰体系中几乎囊括了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 比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等自然神、社区神 (如城隍) 以及伦理政治神 (如圣贤、帝王、英雄) 等等。与其这样认为, 还不如直接就说儒教就是一种民间信仰更为确切些。尽管诸多的儒学研究者不希望也不愿意把儒教的层次拉得如此卑微, 但事实上, 儒教的存在不正是以民间儒学的方式在运作吗?放眼望去, 儒教不再是国教, 不再是意识形态, 官方提倡的只是儒学中的学术体系和道德体系, 而非宗教体系。这种下移的儒学, 民俗 (民间) 信仰化了的儒学, 不正是那种弥散在整个社会中的小传统吗?综合来看, 儒学虽然没有构成西方宗教模式的宗教, 但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宗教性特点。这种宗教性就是儒学下移到民间信仰而表达出来的, 以天人关系为核心构成的“信仰”。这种信仰没有在儒学内部诞生, 却在儒学之外生根发芽, 以“儒化民间信仰”的形式构建了一个中国独有的宗教形态。最终, 这种宗教性的儒学为中国神学政治思想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让专制政治能够循环往复运作两千多年。
儒学宗教性, 本质上是儒学现代化的问题, 是儒学脱离意识形态如何生存的问题。汉代开始生发的儒学宗教性, 就是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现代化”, 向上走政教之路, 向下渗入民间信仰。从儒学与民间信仰两者的关系看, 儒学不是只有政治控制和道德伦理, 而是有信仰的, 儒学的发展是多方向的。巫儒分离、独尊儒术、儒民互补、儒道互补、三教合一、四教会通, 都只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当代新儒家提出的儒学宗教性也无非是“五四”以后面对儒学危机而采取的一种“自我救赎”。儒学的根本精神还是它的经世致用, 是它对社会和现实的高度契合, 是它对政治思想的敏感, 儒学现代化也应该本着这种精神, 因势利导, 而不是抱残守缺。
总之, 承载中国文化的主体毕竟不仅仅是某一小撮精英阶层, 还有广大的底层民众。在古代专制社会, 这些被压制在金字塔底层的人终日劳作、奉献, 却得不到休息, 民主与文化只是一种象征性布施。民间信仰虽然荒诞、怪异甚至低级无趣, 但也质朴、率直, 民众在期待到达彼岸世界或追求内心解脱与宁静的此岸世界中蹉跎。反观所谓正统的儒家文化, 看似高雅、威严、神圣, 却也遥不可及, 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民胞物与”, 哪个又是现世的写照?说到底还不是空中楼阁, 说在今世, 却依然缠绵于虚幻。至少, 从神学政治文化看, 儒学与民间信仰的宗教性是一致的, 都不是宗教, 却有着宗教一样的情怀。
参考文献
[1]吕大吉, 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 (总序)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
[2][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74:3025.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1428.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5:2368.
[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经籍考·子·神仙家[M].北京:中华书局, 1986:1810.
[6]丁毅华.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J].南都学坛, 2001 (7) .
[7]谢扶雅.宗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61, 41.
[8]宋兆麟.巫与民间信仰[M].北京:华侨出版公司, 1990:67.
[9][美]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3:179.
[10]礼记·表记: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80:1641-1642.
[11]尚书·洪范: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80:194.
[12]尔雅·释天: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85:2608.
[13][唐]杜佑.通典·卷四十四:礼四·沿革四·吉礼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84:257.
[14]尔雅·释地: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85:2616.
[15]周桂钿.秦汉思想史:下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28.
[16][汉]王符.潜夫论·卜列[M].[清]彭铎.潜夫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 1985:295.
[17]吴冰.民间信仰的儒学文化底蕴[J].福建宗教, 2006 (6) .
[18]方旭东.儒家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吗?[N].时代周报, 2011-01-20.
[19]李锦全.论儒学思想的包容性及其发展路向[M]//李锦全自选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271.
[20]杜维明.儒教[M].陈静,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49.
[21]赵法生.重构乡村的精神世界[N].光明日报, 2016-01-11 (16) .
[22]刘永华.“民间”何在?——从弗里德曼谈到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C]//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 2009:1-25.
[23]牟钟鉴, 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19.
[2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6.
[25]林存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88.
[26]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11.
[27][德]卡希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81.
[28]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18.
[29]余怀彦.中西宗教观演进的比较[J].世界宗教研究, 1994 (1) .
[30]孙尚扬.宗教的界定与儒教问题[C]//胡军, 孙尚扬, 主编.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75周年华诞暨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35-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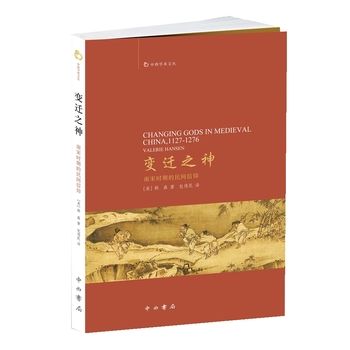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