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泥 粟世来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
白帝天王或曰三王是湘西地区影响最大的本地神祗, 在湘西流传着众多异文。用故事学的方法梳理这些异文可以发现:伴随本地区的社会变迁, 白帝天王传说的核心母题由最初的“威慑”, 后变为“忠顺”, 至清后期转变为“三王之母”, 同时, 神祗的功能也出现相应变化, 从早期的神判, 中期的教化, 发展到后期的赐福。在信仰流变的过程中, 不同的群体都参与了神祗的构建。作为一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 三王信仰中的人与神关系具有典型性。
关键词:
白帝天王; 传说; 民间信仰; 神祗; 母题; 湘西;
作者简介:田泥, 女,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6-12
基金:吉首大学湖南省民族文化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16JDWT011)
Legend of and Faith on Baiditian God
TIAN Ni SU Shil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Jis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legends of Three Gods (collectively known as Baiditian God) , the most influential gods in Xiangxi areas.Collating these legends, we may find that with the local social changes, the core of the legends has turned from the early deterrent to loyalty and obedience, and to“mother of the Three God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36—1912) .Meanwhile, the functions of the gods have also changed correspondingly, from the early divine judgment to the middle education and the late blessing.I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faith, different group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ods.As an important folk faith, Three Gods is typical of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Keyword:
Baiditian God (collective god for Three Gods) ; legend; folk faith; god; motif; Xiangxi;
Received: 2017-06-12
下载原图

白帝天王或称三王, 是湘西地区影响最广泛, 信众数量最多的本地神祗。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六月初一、九月初一等重要的日子, 遍布湘西的大小三王庙宇都会举行盛大或简朴的庙会活动。三王在民众心中的威望极高, 据清代地方志记载, 在人们之间发生争执无法决断时, 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是到天王庙去“吃血”, 之后争议往往能得到平息。由于三王信仰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性, 对白帝天王的研究也成为湘西地区信仰研究的重点之一。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信仰的起源、三王的族属, 分析天王故事演变过程中不同族群及王朝与地方的互动, 多为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在民俗学看来, 在湘西地区流传的三王的故事是民间传说。与作家文学书面创作方式不同, 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 因而不可能有如同作家文学的“定稿”一般最终的固定版本。民间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中被反复讲述, 逐渐形成了不同“版本”, 民间文学称之为“异文”。用民间文学故事学的方法, 将呈现在历史文本中的三王传说分解成若干母题, 通过不同异文之间母题的对比, 可以梳理出故事发展的历时性样貌, 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蕴含的意识与观念。
一
白帝天王的起源已经不可考, 当其第一次出现在明代的史籍中时, 就已经是地方上最重要的神祗了。“白帝天王”之名见于明嘉靖初的《湖广图经志书》中:“鸦溪在县西北镇溪千户所西一十五里, 水自崇山发源, 其流合武溪。鸦溪中有石穴者七, 渊深莫测, 名为龙井, 溪之旁有鸦溪神庙, 其神为白帝天王。每岁六月已日起至已日止, 忌穿红张伞吹响器。山林溪涧, 虽有禽兽行走并鱼跳跃, 人不得名, 亦不敢取。”">[1]1454提及了白帝天王庙所在的位置及每年祭祀的时间。另见于明代朱辅的《五溪蛮图志》中:“在镇溪南七里。其神为白帝天王。风俗畏鬼神, 于六月辰日至巳日, 忌者即是名曰‘龙蛇大会’。盖南方所尊之神, 其所从来与名氏, 则无所考据也。”">[2]139指出了天王庙的位置和祭祀时间, 并特别指出, 天王的来历不可考。从明代的文献可见, 当时记录者对于天王来历无可稽录, 无论这“不可考”的原因为何, 可以推测的是, 在明代, 天王的传说并不兴盛。这种情形到清代发生了变化。康熙四十二年, 阿琳采集到天王的传说并记录下来:
乾州之东北鸦溪, 有天王庙在焉。其像衣冠而并坐者三。询之土人, 曰此北帝天王也。姓杨氏, 兄弟三人, 长曰金龙, 仲曰金虎, 季曰金彪, 皆宋时骁将。孝宗朝, 溪蛮为害, 奉命徂征, 杀伤甚众。时值炎暑, 王憩枫林下, 渴饮溪流, 中毒而殒。未几, 王遂降神于蛮, 疫疠大作, 苗人死者过半。众皆震慑, 因祷而祀之, 誓不敢怠。一云, 王开九溪十八峒, 追蛮至五寨司奇梁洞, 斩其渠魁及余党九千余级, 遂平其地。孝宗嘉之, 锡以王爵, 民怀其德, 蛮畏其威, 故立庙以祀, 呼为北帝天王, 尊之至也。 [3">阿琳.红苗归流图[M]//段汝霖.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长沙:岳麓书社, 2008. </a>][3]243-244
在此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白帝天王的来历在明嘉靖朝还无可考证, 一百多年后出现的这两个异文从何而来?分析阿琳的这两个三王的传说发现, 这两篇异文情节大同而小异, 共同母题有三:杨氏兄弟、杀苗、殁后为神, 可以视为天王传说的核心母题。在与其他传说比照后发现, 具有这三个核心母题的传说在清代以前早已广泛流传, 比如明代已见记载的飞山传说。飞山公是湘黔交界地区常见的民间神明, 至今在湘西中大多数乡村都还能够见到飞山庙。《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九载靖州有威远侯庙, 并注:“在州西, 侯名再思, 诚州刺史, 杨氏之祖, 宋绍兴间封威远侯, 立庙祀之, 淳熙闻加号英济, 后庙毁, 本朝正统十一年重建, 正德中参将黄焘重修。”靖州通道县有飞山行祠, 绥宁有飞山庙, 注云:“其神即靖之飞山寨人, 兄弟勇敢累破苗贼, 殁而为神, 元时每著阴助, 国初封威远侯, 血食此上。”对比明代的两篇飞山传说, 其母题与清代天王传说相近, 尤其后者, 包含了康熙年间白帝天王传说的几个重要母题:杨氏兄弟、杀苗人、天子封爵。
核心母题的一致, 让白帝天王传说的来历变得有迹可循。再查阅明清两代的地方志, 明代的地方志中飞山庙的记载见于湖南靖州、通道、绥宁以及贵州的黎平、思州、镇远等府县 [4">廖玲.明清以来武陵地区飞山庙与飞山神崇拜研究[J].宗教学研究, 2014 (4) . </a>][4], 湖南境内的其他府县均不见记载。到乾隆年间泸溪县和永绥厅出现了飞山庙的记载。泸溪县的飞山庙在当时已经被毁, 永绥厅的“在城西七十里茶峒村, 乾隆十六年里民建”">[5]349。茶峒在酉水支流清水江边, 上通松桃, 下达常德, 远至汉口, 泸溪县的浦市正在沅江边上, 商贸往来极其繁荣。可见大约是在明至清初期间, 在清水江、沅江上往来的客商将飞山信仰传播到此。随着飞山信仰传入的, 当然还有飞山的传说。飞山信仰在湘西传播的过程中, 飞山神的传说与本地的天王信仰结合, 成为民间解释天王信仰由来的故事。这种“移植”在民间传说的传播过程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产生于山东, 随着山东人闯关东而传播到了东北, 并成为解释当地的黑龙江名称由来的传说 [7">段汝霖.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M].长沙:岳麓书社, 2008. </a>][6]72-74。飞山传说与白帝天王信仰结合后在民间应该是流传甚广, 以至于段汝霖在撰写《楚南苗志》时将白帝天王误认为飞山神">[7]178。
飞山神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震慑苗人。在万历年间贵州铜仁知府撰写的昭告文中就曾提到, 当地的飞山神庙在“苗乱”中被毁, 须重建神庙以帮助御苗 [8">张应强.湘黔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的形成与流播[J].思想战线, 2010 (6) . </a>][8]。由于信仰的广泛传播, 白帝天王的传说也随之深入人心。随着白帝天王传说中屠杀苗人情节的不断讲述, 天王的形象更加威严可怖。在传说中, 神拥有比人强大得多的力量, 能随时给人降下灾祸, 夺人性命。这种杀伐由于缺乏对原因或标准的说明而显得益发可怕。白帝天王这个神祗对苗人来说就是三尊不敢冒犯的恐怖凶神, 以至于“其入庙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 (《乾隆凤凰厅志·卷十四·风俗》) “过庙不敢仰视”“苗酋皆惧, 缩不敢进。” (《乾隆凤凰厅志·卷二十·艺文》) 天王的神力如此强大可怕, 如同一张大网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人们相信, 当有事争执不下时, 能给予最终判决的, 只有天王。到天王庙“吃血”就成了最后的解决途径和方案:“凡有祈祷, 或冤忿不白, 而欲誓者, 则往庙告神。其远不能赴庙者, 告于拜亭。去乾为中道, 乃神之行祠也。凡誓, 小事以鸡, 重则以猫, 刺血滴酒中, 各饮以明心。其誓必曰:我不冤你, 你若冤我, 我大发大旺, 我若冤你, 死我九十九代。盖云祸且延及子孙也。”">[3]244
由飞山神传说移植而来的“杀苗”母题, 在明末清初“苗乱”不休的湘西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在史籍的记载中湘西苗族人极为“好斗”, 且一旦成仇, 累世不休。在地方志中屡见湘西苗人“打冤家”的记载:“语言财利一有不平, 怒气相加, 遂成争斗。言告蛮长, 剖析曲直。唯以曲者财物偿其直者。名日‘包裹’。有杀人之仇不能报复者种植树木以纪岁月, 祖孙相承, 必杀其人而后息。”">[2]73“苗人偶遇争竞不平, 深仇夙怨, 欲拿人抵事, 骤难即得, 而忿不可释, 则有所谓打冤家者。……死者之子若孙, 植树墓旁, 以记其恨, 转相仇杀, 滋蔓无已矣!” [17">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M].周星, 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a>][7]175-176这种冤冤相报世仇结成以后, 除了带来敌对双方的两败俱伤, 别无益处。
从文献来看, 清前期, 人们更多地是强调天王神在解决民间纠纷上所具有的审判权威 [9">龙圣.晚清民国湘西屯政与白帝天王信仰演变[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a>][9]。事实上, 在很多情况下, 人们的忿争是很难判断对错的。证据的缺乏或各执一词, 或年岁久远, 细节淡忘等等, 第三方无法为争执者给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判决。当事双方都声称自己无辜, 指责对方的过失, 人类的智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在此种情况下, 人们只能求助于天王神所具有的神圣权威。在双方对其信仰的神灵, 怀着相同的信念发誓的时候, 他们会坚信, 向往中的正义必定会到来。因此, 这样的超自然的“判决”给予了人们希望得到的公正。因而, 秉持着“神意”的判决就成为了终极的裁判, 对此结果双方再无异议, 也不敢违背。纷争得以以一种相对来说相当简捷的方式解决, 这种方式付出的成本也是最小的, 因为它成功避免了由于双方的敌对可能导致的损失。
二
清代前期对湘西地区来说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康熙四十二年 (1703) , 清廷以“红苗抢掠, 地方不靖”, 派礼部尚书席尔达统帅满汉大军至镇筸征剿。军队从四路攻打“违抗”的天星寨、打郎寨、毛都塘、糯塘山等苗寨, “诸苗慑服, 愿输课为良民”。镇筸地原分属镇溪千户所、筸子坪长官司及五寨长官司, 四十二年用兵成功, 四十三年裁撤了镇溪千户所、筸子坪长官司。在镇溪置乾州厅, 设同知, 将原镇溪所六里苗民编定户籍, 归汉纳粮由乾州厅管辖。雍正八年 (1730) 六里设同知, 赐名永绥协。在原筸子坪长官司辖地置凤凰营, 设通判, 后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凤凰营改凤凰厅。雍正十二年 (1734) 茅岗土司改土归流, 至此湘西地区改土归流全部完成。
改土归流, 开辟苗疆后, 帝国官员们很快发现, 比起“开辟”而言, “治理”显然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由于经营地方的需要, 官员们深入苗地, 实地了解了苗族民众的生活。此时的苗人在帝国官员们的笔下几乎处于“蛮荒”的状态。农业非常落后, 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由于武陵山区, 山多田少, “种稻谷者无几, 俱种杂粮”;没有文字, “言语殊离”;有打冤家、伏草的恶习。苗人的家庭也没有汉人家庭严谨的“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纲常, 一家人往往“翁姑子妇兄弟妯娌男女杂卧并无间隔” [10">王玮.乾州志:卷四:红苗风土志[M].刻本.1739 (乾隆四年) . </a>][10]。这是一群一直以来“无君长, 不相统属”, 归附不过数十年的“化外之民”。他们与内地汉人风俗迥然有别, 言语不通, 且几千年来叛乱不绝于书。可以想见, 对于帝国官员来说, 面对这样的民众, 如何管束、教化他们, 是颇为头疼的事情。
依照治理边疆和蛮夷的历史经验, 官员们在治理苗疆上采用的是“德威”并用, “兵礼”兼具的策略。乾州同知王玮谈到对苗人的“控御”之策时认为:“德威二者, 一有或偏吾未见其可也。”“德”的方面, 王玮注意到了苗人中诸多祭祀鬼神的风俗, 因此提出“化导之法, 当秉其信巫畏鬼之习, 动以祸福□□□□□之, 可渐消其残杀暴厉之心” [10">王玮.乾州志:卷四:红苗风土志[M].刻本.1739 (乾隆四年) . </a>][10]。一方面要利用苗人对巫鬼的信仰, 用祸福报应的观念对其进行“化导”, 以期能约束其行为, 改变其好斗轻生的惯习。另一方面, 也要在苗疆周边布置兵力戍守。“防范之法”“不如使民自相为卫, 则团练之法所当行也。”“苗疆三厅”中的其他两地, 时任凤凰营通判的杨盛芳与永绥同知段汝霖在利用民间信仰“教化”苗人的策略上与王玮是不谋而合的。段汝霖认为:“夫苗俗敬神畏鬼, 谓法可幸逃, 而神不可欺, 其先务也, 宜动之祸福、报应, 勉其为善去恶。”">[7]199杨盛芳也认为:“ (白帝天王) 为民苗所畏服, 不妨因其俗而治之。” [11">杨盛芳.凤凰厅志:卷十:祀典[M].乾隆丁丑年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a>][11]段与杨都看到了民间信仰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考虑到了利用民间信仰教化民众的可能性。
在乾隆十五年成书的段汝霖的《楚南苗志》中, 出现了这样一个版本的三王传说:
里老相传, 杨姓, 为辰州人。一云靖州人。兄弟三人, 乃宋时骁将, 智勇兼备。因苗人出没为害, 领众击之。知苗性素贪饮食, 时值天气严寒, 乃多宰牛豕煮之, 悬林木间, 群苗争相取食, 乃出其不意大破之。遂开九谿十八峒。仅存五姓残苗, 即今之昊、龙、石、廖、麻等族是也。厥后, 反命人忌其功, 遗以毒酒, 将以王命, 兄弟饮之, 同时俱没。时正小暑节也。 [7">段汝霖.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M].长沙:岳麓书社, 2008. </a>][7]
在这个故事中, 三王之死这个情节颇有深意。故事说道, 三王是饮用毒酒殒命的, 但未明确指出毒酒的来源。清晰指明毒酒来源的是另一篇异文。江德量的《白帝天王》未被王玮纳入《乾州志》, 但被收入了《广虞初新志》中。“白帝天王, 湖南乾州鸦溪人, 姓杨氏。母感龙而孕, 一产三子, 各有勇, 武艺绝伦。遇有苗人不靖, 集村民歼之。尝以三十六人斩叛苗九千, 时南宋渡后也。朝廷闻之, 招致杭赐爵, 见其状貌英异, 恐为边患。颁以鸩酒令归, 供妻孥酌之。未至家, 苦热开瓶, 取饮, 三人俱中毒死, 而灵不昧, 屡著神异。官民立庙祀之, 称白帝天王。第三郎尤显应。” ( (清) 黄承增辑《广虞初新志》卷38, 《白帝天王》)
将这一时期的传说与康熙时期的传说在母题上进行对比可以看到, 在乾隆时期段与江的天王传说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母题:帝赐毒酒。在这两个时期的传说中, 白帝天王身份都是帝国官员, 但是乾隆时期的异文出现了天王奉诏觐见皇帝的环节, 在地方官员与一国天子的互动中, 天王臣子的身份得以确认, 皇帝的君主身份得以确认, 或者可以说, 觐见其实是认同湘西苗疆作为帝国版图之一部分, 认同王朝中央在湘西之行政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此外, 在阿琳的异文中, 天王死亡的原因是饮用了溪水中毒, 在江的异文中是皇帝的毒酒赐死。在王朝国家, 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 不仅可对官员进行任免、赏罚, 甚至可对个人生命生杀予夺, 作为臣下必须对皇帝命令绝对的服从。帝赐毒酒这一表达皇权至高无上权威的母题被郑重凸显, 且细节丰富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在汉族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 在此时的苗人中却是一无所知, 因此, 对湘西苗人的教化首要之义在于教导其了解和遵守当时社会中通行的伦理准则, 而对于这些几千年来“无君长, 不相统属”的“生苗”来说, 其中尤为重要的, 莫过于五伦之首的“君臣之义”。即要让这些才编入户籍不久的苗人认同并服从作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在这一忠顺的母题表述中, 帝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们试图让百姓明白, 三王这些本地神勇无匹、万人景仰的英雄, 无论功劳如何显赫, 皇帝也有权力随时轻易地夺走他们的性命。而为臣民者, 对于皇帝的任何命令, 只能俯首顺从, 这是为人臣子的义务。
三
“改土归流”后的“承平”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乾隆六十年开始, 湘西爆发了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这场起义前后持续了12年, 涉及凤凰、永绥、乾州三厅, 四千多苗寨, 人口近四十万">[12]157。起义后, 湘西人口、经济都受到了重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整个苗疆约四分之一的村庄被毁, 受到影响的家庭可能达到了25 000户, 直接焚毁的房屋25 000余座, 无家可归者10余万人">[13]90。损失人口绝大部分为成年男性。在战后家园的重建中, 劳动力的匮乏对于帝国官员和普通百姓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在战争中无数家庭中的父亲、儿子、兄弟、丈夫死于战场。湘西的家庭往往是以核心家庭为主, 儿子成年娶妻后往往分出另住, 因此, 一个家庭的成员主要是父母与孩子, 可以想象, 在这样的家庭中, 成年男性的失去, 其影响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不啻于灭顶, 而亲人的逝去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悲痛也不言而喻的。而在湘西地区, 遭遇战争灾难的家庭成千上万。
乾嘉起义后, 湘西地区百姓尤其是苗族人从经济到心理所遭遇的困境如此严重, 一威严或忠顺的神祗在这样的情境下都已经不合时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乾嘉之后的天王传说与天王信仰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光绪凤凰厅续志》中记载了一篇非常详细的三王传记:
三王降神之始末:本龙种也, 为靖州蒙姓外孙, 嗣继于渭阳杨氏……当宋徽宗朝, 有杨昌除者, 官昭信校尉。重和二年, 以剿平皮历、竹滩、古州八万苗蛮功封显武将军, 复讨降靖州瑶仡佬, 授宣抚军民总管, 专制靖州。……每化人形, 巾服丽都, 居然雅士。渐与近村蒙翁交厚。蒙有田沿洞侧, 恒忧乏水。一日私祝曰:“有能泽兹荒瘠, 吾当以女妻之”。灵锐自承, 俄而塍畔泉生, 遍成良沃, 蒙遂赘灵为婿。居岁余, 了无他异, 惟豪饮千觞不醉, 为众所惊。……蒙女戏语家人曰:“郎平日不吉酸, 今试置醯酒水, 或可醉也。”如其言。灵醉, 奋现龙形, 拏雾攫空飞去。女娠失耦, 痛悔莫追。是年五月五日申时一产三男, 状皆魁猛, 命名金龙、金彪、金纂, 即三王也。……载名杨氏乘, 嗣为己后……三人去到临安, 后遭奸臣谋害。">[14]371
在苗疆三厅中的乾州厅的方志中, 在同一时期记载的三王传说也有了新的情节:
雅溪距乾五里地, 惟杨氏一族。世传有室女浣于溪, 忽睹瑶光, 感以人道, 逾年一产三子。长俱英勇, 体貌迥别。三厅红苗暨沅靖一带苗不靖, 侯屡率所亲痛剿之。……苗畏如神。殁亦显灵……故奉祀惟谨焉。雅溪庙后祠祀侯母, 雅溪最亲昵, 无老幼男女入祀不呼为老姑婆, 花冠绣履, 任小儿嬉弄于前不为亵。他处无侯母祠。 [15">林书勋.光绪乾州厅志:卷四:典礼[M].光绪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a>][15]94
这两个三王传说中都出现了一个三王之母怀孕生子的母题:三王之母。在这两个版本的传说中, 三王的母亲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 均交代细切。在这一叙述中, 三王之母宛然一生活在身边的邻居。这种真实的细节带来了巨大的亲切感。也正是这种如邻家女子般的亲切感, 有效地化解三个王爷高高在上的威严肃杀之气。而怀孕生子这一情节, 使得杨氏女成圣后具有了母性仁慈的光辉。当这些失去亲人的女子们跪拜在杨氏神像前祈祷时, 她们内心显然会因为三王之母与她们同为女子, 同为母亲, 更能理解她们的苦楚和祈求而感到安慰。三王之母的塑像进入庙宇供奉后, 求子便成了人们进入三王庙祭拜的重要理由。而随着龙之子母题出现, 人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降雨之职, 也列入到了三王的名下">[16]539。
四
当谈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时, 学者们往往提及中国民间信仰的“现世性”、“功利性”等特点。如认为民间信仰的基础是“现世利益”">[17]18。与制度性宗教追求的终极的灵魂救赎相比, 中国民间信仰更注重的是此世此时的需求满足。还有被众多学者论及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 把灵验与否当作信仰的前提, 期求直接的物质效益 (或降雨, 或病愈) , 极少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升华">[18]250。多神, 给崇拜的神灵增加职司等">[19]9。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 或许可以从白帝天王传说的个案来窥见一斑。
由明至清三百余年间, 白帝天王传说的母题历经演变, 同时, 三王信仰中神祗的功能在与传说的互动中,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白帝天王的传说是由众多民众集体参与的口头创作, 是经由口头的传播而在不同地区和民众中流传开来的民间文学文本。这种口口相传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导致了一个与文本创作相比泾渭分明的特性。居于传说流传地的民众, 在听到传说后再行转述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有意或无意, 自觉不自觉地渗入自己的感受、思考或评价。因此, 在民间传说的流传过程中, 每一个传说的讲述者, 不仅是在参与传说的传播, 也是在参与传说的创作。这些匿名的讲述者, 都可以参与到传说的创作中, 对传说进行修改。与文本创作会有“定稿”的情形不同的是, 传说几乎不会有定稿, 只要传说还在流传中, 还在某一地区具有生命力, 那么, 所谓的“版本”便不会确定下来。
白帝天王的传说是对天王信仰的解释, 或说明神祗的由来, 或说明某些仪式的内涵, 或强调神祗的合法性。民间传说的口头性特征使得每一位参与传播的故事讲述者都可能是一新版本的创造者, 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能在传说中加入自己对神祗的感受、理解和评价, 也能出于自身的需要, 赋予神祗以新的功能。当这些感受、理解和需要能引起他人的共鸣, 便能得到肯定以及认同, 这一版本的传说便流传开去。因而在传说的不断生成中, 传说的讲述者, 或信众们, 同时在其中参与了信仰的构建过程。而制度性宗教中, 以犹太—基督教为例, 公元一世纪末, 《旧约》正典化结束, 公元三世纪末, 《新约》正典化完成 [14">侯晟, 耿维中.凤凰厅续志:卷一:典礼[M].光绪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a>][20]41,147, 至此圣经的正典化全部完成, 从此不再接纳任何文本进入正典。而对经典进行解释的释经权自古至今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经过千年的阐释累积, 上帝被认为是在要求人生的完全服从, 被视为“主”、“王”以及“父”">[21]25, 这是经宗教权威们公认的上帝的属性, 普通信众只能接受和遵从。
由此可见, 与制度性宗教相比, 民间信仰最大的特点在于神与人关系。在犹太—基督教中, 上帝是主宰, 全知全能, 人是他的造物。上帝与人的关系既如父子, 又像主仆。人必须绝对服从上帝。而在民间信仰中, 民众能直接参与到神祗相关的传说的创作, 而这些传说作为对神祗来源、仪式意义、神祗功能等做解释说明, 是一开放的体系, 在这开放的“话语场”中, 所有人都有可能就自己对神祗的理解发表看法, 从而影响信仰的生成和走向。对于能够塑造神祗的形象, 赋予其神圣的属性和功能的信众们来说, 他们必然会按自己的需求来建构信仰。因而就神与人的关系来说, 如果犹太—基督教中神人是主宰与崇拜者的关系, 那么在白帝天王信仰中神人更像是守护者与被守护者的关系。在信众看来, 神祗如守护神般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 存在于自己的身边, 几乎能满足自己的任何愿望, 因此能在此生此世满足的需求, 也就不必延宕至未来某个未知的时间;如能回应首要的物质需求, 所谓精神的超脱也就可以靠后了。
参考文献
[1]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辰州府:山川[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2]沈瓒.五溪蛮图志[M].李涌, 重编, 陈心传, 补编.长沙:岳麓书社, 2012.
[3]阿琳.红苗归流图[M]//段汝霖.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长沙:岳麓书社, 2008.
[4]廖玲.明清以来武陵地区飞山庙与飞山神崇拜研究[J].宗教学研究, 2014 (4) .
[5]席绍葆.乾隆辰州府志:卷十八:坛庙考[M].乾隆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6]李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10.
[7]段汝霖.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M].长沙:岳麓书社, 2008.
[8]张应强.湘黔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的形成与流播[J].思想战线, 2010 (6) .
[9]龙圣.晚清民国湘西屯政与白帝天王信仰演变[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10]王玮.乾州志:卷四:红苗风土志[M].刻本.1739 (乾隆四年) .
[11]杨盛芳.凤凰厅志:卷十:祀典[M].乾隆丁丑年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12]吴荣臻.乾嘉苗民起义史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13]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4]侯晟, 耿维中.凤凰厅续志:卷一:典礼[M].光绪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5]林书勋.光绪乾州厅志:卷四:典礼[M].光绪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6]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7]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M].周星, 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18]金泽.中国民间信仰[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19]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0]梁工.圣经指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21]约翰·希克.宗教哲学[M].何光沪,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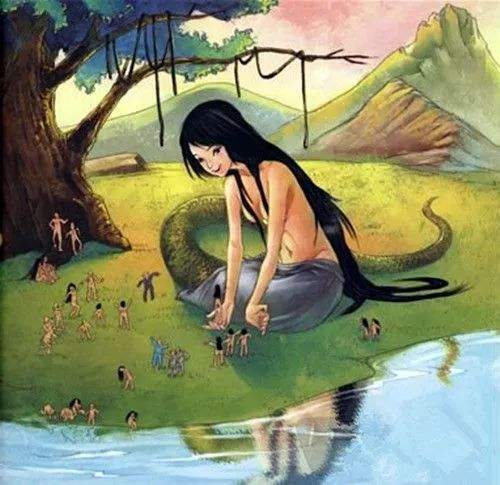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