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祝平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 要:
中国的民间信仰蕴含着公益慈善的道德力量, 积极参与养老公共领域的建构和行动是传统民间信仰“转化创新、开放包容、形成合力”的重要选择, 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自我调适的内在要求, 有助于传承崇德敬祖、尊老爱老文化基因,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纵观浙南L村西门宫的养老参与实践, 民间信仰可以成为官方和民间养老事业的重要补充。而且, 由于民间信仰厚植于民间, 兼具广泛的群众性、独特的宗教性、丰富的娱乐性和浓重的伦理性, 在乡村社会的养老参与中, 相较于规范性的宗教组织和一般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有独特而明显的优势。同时, 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子系统, 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方式和效度与政府参与、政教关系、市场发育、社会信任以及对现实制度环境的适应等密切相关。促进和便利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 需要以主流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转化创新, 增进社会认同;以规范场所管理为基础, 坚持开放包容, 引导社会自愿有序参与;以尊重老人实际需求为导向, 倡导互助共享, 涵养向上向善、敬老爱亲文明乡风;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推动形成民间信仰有效有序参与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The Old-age Care Participation of Folk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Rural Society
ZHANG Zhuping
H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lk beliefs in China contain the moral power of public charity.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of old age ca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hoice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belief“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formation of synergy”,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self-adjustment of folk belief in contemporary society.Itishelpful to inherit cultural gene of moral worship, respect for ancestors and elders, and to promot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building.A general survey of old-age care participation at Ximen Palace in L Village of south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that folk beliefs can b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official and civil old-age care career.Because of growing among folks, folk beliefs have widely mass feature, and with rich entertainment and strong ethic.Compared to normativ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general civi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olk beliefs also have their unique and obvious advantages at old-age car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ommunity.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subsystem of rural society, the method and validity of folk beliefs in old-age care particip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lations, market development, social trust and its adaptation to reali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old-age care participation of folk beliefs in the rural society, it needs to lead by the mainstream values, adhe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enhance social identity.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emises serves as the basis to adhere and to guide the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 voluntary and orderly manner.Guided the respect to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we should advocate mutual sharing, conserve the civilization of up to the good, respect elderly love family.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we sh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folk beliefs participation in an orderly and effective to the old-age car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一、研究缘起
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 蕴含着公益慈善的道德力量, 具有济世利人、服务社会的传统功能。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 神灵、庙宇、仪式及相关信仰组织形态深深嵌入中国乡村社会, 始终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紧密粘合, 彰显了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也体现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力。
中国改革开放后, 国家高度重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宗教因素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共中央先后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1) , “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2006) ,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11) , “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2015) 等方针, 并制定“关于做好民间信仰工作的意见” (2015) 以及作出相关部署。这些既表明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宗教因素已成为新时期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更为积极引导民间信仰更好融入当代社会、服务当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基本依循。
近十余年来, “积极引导民间信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1) , 社会公众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民间信仰的认知逐步转向“积极评价增多” (1) 。与此同时, 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公益慈善养老服务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并进入了学者的视野。目前,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状的梳理。比如, 甘满堂 (2) 等分别对湖南浏阳和福建地区部分宫庙的公益慈善支出情况作了深入调查, 表明“为村落老人协会提供资助”“救济困难老人”和“ (给老人) 免费送药与义诊”等已成为一些民间信仰场所的历史常规。二是趋势的调研。比如, 林国平以福建地区“三一教”为研究对象, 认为参与公益慈善和养老服务已成为当代乡村庙宇较为普遍的现象, 并且覆盖面趋于广泛、投入量趋于增多、方式上趋于多样;同时指出, 当代民间信仰介入乡村社会公益慈善, 可在社会上形成较好的影响, 社会作用不可低估 (3) 。三是平台机制的考察。比如, 林国平2005年在福建部分地区开展民间信仰调研时就发现, 福建省的有些乡村宫庙已经建立了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领导机构, 认为这能“更加有效地开展 (这项公益慈善工作) ” (4) ;李向平基于对陕北乡村民间信仰当代状况的调研, 认为当代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可以依托乡村组织, 建立起共同信仰的乡村社区, 开展乡村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 (5) ;肖健美 (6) 等认为, 参与公益慈善和养老慈善是体现民间信仰 (宫庙) 价值的最佳方式, 应主动与地方政府、社会各界 (包括学术界) 互动, 创新公益慈善参与机制、方式和领域, 谋求自身健康发展。
学界已有的观察和思考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的认识, 即在中国乡村社会养老服务领域, 民间信仰公益慈善古已有之, 形式多样, 并形成了一些较好的传统, 较之于宗教组织及其它社会组织的慈善养老参与, 或许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在活力, 可与农村老年社会建设形成良性的互动。当然, 相较于乡村社会的丰富实践, 学界在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已有的成果大多是一些数据的罗列或资料的累积, 缺乏对民间信仰养老参与中相关主体及其作用对象的研究, 对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发生过程、发生机制和作用机理、制度风险等关键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
“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问题更为严峻。我们认为, 当代民间信仰的恢复发展与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变迁两大主题相互契合、相互作用, 为规范创新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模式和提升民间信仰社会服务能力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倡导复兴传统文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以及乡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的背景下, 应该本着立足乡村社会实际和群众需求导向, 按“创新转化、开放包容、形成合力”的要求, 深入开展相关研究, 探索推进和规范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政策路径, 为中国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转型和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丰富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二、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历史形态及当代实现机制
(一) 一个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图景
本文重点考察的样本村———L村是浙南沿海地区一个普通的传统村落, 历来以农耕、近海浅水捕捞和滩涂作业为主。因濒临海域, 自然灾害频发, 村民以农为生异常艰难。改革开放后, L村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 快速步入了“亿元村”行列。当地人几乎家家办企业、户户搞经营, 全村80%以上的青壮劳力不常在村里居住生活, 外出人员以求学创业、经营企业、为家庭工厂“跑业务”和打工为主;外来人口众多, 约占户籍人口的50%, 以在当地村民所办加工、制造类企业打工为主。截至2016年底, 村户籍人口656户3 080人, 人年均收入达2.58万元, 村集体收入达300余万元;全村60岁以上人口有670人, 占户籍人口的21.75%, 65岁以上人口有470人, 占户籍人口的15.26%, 表明L村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区。
“村村皆有庙, 无庙不成村”是江浙一域农村的普遍写照。L村现存有两座宫庙———西门宫和东岳观。西门宫是L村所在县域内最早建立的民间信仰场所之一, 而且是唯一的一座以妈祖为主要供奉对象的庙宇, 始建于何时迄今尚未见确凿之史料, 但至少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渊源 (1) 。据村里老人回忆, 民国时期的西门宫仅十余平方米, 时当地名绅热衷于料理小庙事务, 并常带头捐助功德, 维系庙宇维修各项支出, 至年尾有余款则以庙宇之名救济村里老弱, 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2)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 西门宫与周边村庙一道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的洗礼, 庙宇仅留墙基、神像不知所踪。1970年前后在村里老人的带领下开始原址复建, 此后又历经多次重修和扩建, 并争取纳入了宗教场所管理 (3) 。如今的西门宫有主殿1个, 高13.8米、占地1 158平方米, 还有辅助用房若干共730余平方米, 可谓“巍峨壮丽、颇具规模”。主殿所供奉的神灵也由旧时单一的妈祖, 发展而成包括妈祖、陈十四娘娘、水荷娘娘、送子娘娘、财神爷、观音大士、三官大帝、太岁爷爷、文昌爷、土地爷等十余尊, 几乎涵盖求子、求财、求学、求寿、安土等人生诉求的方方面面。调研发现, L村西门宫中安置神像的不断增多, 既是近30余年来当地历次村庙“拆、改、并”整治的结果 (4) , 更是在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中村民不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是村民对于流动中的生产生活世界的深沉情感的外向流露。
东岳观始建于宋代, 供奉的主神为东岳大帝。自建立以来, 即为道教场所, 一直由道士主持宫庙事务, 然除此之外, 在L村民众看来, 它与西门宫似乎并无异处。“两座庙村里人都会去 (拜) 的, 都很‘灵’” (5) 。据笔者考察, 两处信仰场所虽同在L村, 有着重合度极高的信众群体, 相近的信仰仪式、相似的场所构造等, 但在崇祀对象上和祭拜目的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信众在西门宫的祭祀更注重祈求平安美满和对现世的关照, 而在东岳观的祭祀更注重祈求趋灾避难和对往生的关怀, 因此, 在崇祀对象上也不尽相同。当然, 前往两处场所祭祀的信众所处的境遇和情绪状态也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 L村的老年人日常更愿意在西门宫活动, “这里 (指西门宫) 地处村里的中心位置, 是老年人主要的聚会场所, 还是村里的‘百姓故事会’, 凡村里村外、家长里短各种新鲜事 (老人们) 都会在这里发布、讨论” (6) 。或许, 这正是西门宫人气更显旺盛、更能聚合老年村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实践形态及特征
“慈善是行动中的信仰体现。” (7) 以历史的维度, L村西门宫养老参与的形态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单向性和单一性:新中国成立前, L村大族乡绅主导下的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
如同其它多数乡村庙宇, L村西门宫少有历史文献存留, 数百年的历史多为当地百姓口口相传、代代相承, 一定意义上说, 随着村落中一代人的消失, 村庙变迁停留在他们身上数十年的印记也将随之消逝。在村里访谈时, 少数年长者还可以部分回忆起民国后期自己所体验的西门宫信仰, 或其父母辈给他们讲述西门宫香火盛况的只言片语。张氏是L村的大宗族, 外出营生者众多, 并常有获得功名晚年归乡者, 他们热心主持村落公益, 整饬乡约风俗, 尽己所能影响和关爱乡里。民国时期的西门宫即设有管理小组, 主持者即是当时张氏宗族名绅。此时, “宫庙规模虽小, 但坚持护修、悉心管理, 香火一直很旺盛, 信众络绎不绝”;“庙会每年定期开展, 村里的老人可以施展各种本领, 庙管还安排村里老年人看戏、聚餐, …… (庙管) 也会借机帮助一些老人教育晚辈, 并给困难老人施舍 (财物) ”;“还有的外地亲友借看庙会来走亲戚 (看望宗族长者) , 村里老人都特别知足。” (1) 普遍贫穷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最突出特征, 以围垦滩涂维持生计的L村民众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见。然而, 大族乡绅名望借助村落最核心的公共平台———西门宫及其最重要的群体性活动———庙会而施以善意, 使得在困苦条件下生存更为不易的L村老人却因西门宫之信俗而获得了少有的身心愉悦体验。包括通过庙会展示才艺而获得更多认可的机会, 通过庙管帮助教育晚辈而获得更多精神宽慰, 通过获得施舍以更好缓解燃眉之急, 通过共同祭祀聚会亲友而促进团结和睦宗族的愿望得以更好满足等。
无疑, 所有这些皆因信仰之名而更为坦然, 也因信仰之名而大大消减村落内部的阶层隔阂, 使主流社会阶层个体的助老扶弱善意得以更有效的实现, 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乡村社会敬老、爱老、助老的风尚。当然, 显而易见, 这一时期L村西门宫的养老参与是由大宗族乡绅名望主导的, 个体性、单向性慈善行动, 它的实现程度与上层社会个体荣耀宗族的心理、回馈乡里的意愿与满足程度以及善意指向等密切相关, 具有施舍性、随意性、临时性和不稳定性。
2. 互动性和互助性:改革开放后新型村落精英推动下的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民间信仰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不断被强化的“封建迷信”烙印, 传统信仰习俗进入了沉寂期, 一度萧条。在L村, 西门宫的喧嚣虽然隐退, 但却常常零星绽放, 即使没有宫庙和神像, 香火却从未中断。至改革开放后, 村落当中一些商品经济的弄潮儿, 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劲头博得第一桶金之后, “不仅没有忘记西门宫, 而且加倍的‘报偿’西门宫” (2) , 宫庙活动的捐资款项逐年增加。初始几年, 在村落大姓宗族长者的操持下, 这些快速成长的“新型村落精英”多会仿照“旧制”, 捐资修庙、举办庙会、酬神演戏和以庙会之名邀村落中的年长者聚餐, 并以宫庙之名给予村落中的鳏寡孤独者物质帮扶。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村落经济的繁荣和村民收入的迅速增长, 西门宫的香火也达到了空前的旺盛。相形之下, 仅十余平米的祭祀场所已然捉襟见肘, “与村庄的繁荣景象极不相称”。同时, L村产业结构转型之后, 原本少量的农地也被建成了厂房, 以耕种为业的老年人迅速呈现“集体失业、无处可去”的状态, 急需为他们找一个“安置”之所, 西门宫无疑成了共识度最高的首选。于是, “在村里几位老板的倡议下, 村民积极响应, 很快就推举成立了以11名老人为首事的管理小组, 专门负责西门宫的重修扩建和日常事务。”正是在新型村落精英的积极推动下, 在村落老人不遗余力的谋划操持下, “几乎整个村子都被动员了起来, 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重修扩建后的西门宫除祭祀主殿, 还设置了戏台、食堂、文化室、电脑室等, 为村落老人日常的交流、信俗参与以及学习、生活、娱乐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平台, 使“心养”“身养”“学养”相结合的互助养老成为可能。
“神因人而圣, 人因神而安”。重修扩建后的西门宫恢宏敞亮、香客熙熙攘攘, 在宫庙管理小组和信众的悉心打理下整洁有序, 成了L村老人聚会、交流、分享信息、展示才艺以及议论家情村政的理想场所。日益隆盛的香火也为西门宫带来了可观而稳定的经济收入。凡每月初一、十五和神诞日以及庙会期间老人们都会到西门宫聚餐, 餐资多由宫庙中的善款支出, 老人们也时常从自家带些粮食菜品等用以供奉神灵, 然后供众人分享。同时, 相对年轻的老年信众则会主动承担起制作饭菜的任务。据近几年西门宫公布的善款收支账目清单, “补贴村里老人的福利”和“老弱灾贫救济”等是每年节余款支出的规定项目, 也是最大的支出项目。
不难发现, 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长起来的L村新型村落精英是西门宫历次修建扩建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推动者, 也是宫庙较可观稳定的善款收入得以持续的重要成就者, 使得西门宫的壮大与其养老参与的深入拓展实现了“共生”。其实, 村落精英及其他村民信众不断向西门宫捐助功德善款,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财富的聚散现象, 以信仰之纽带产生“聚散效应”, 客观上也有助于村落社会的互助共享与和谐共生。新型村落精英的推动、村落老人内在激情的点燃和诉求的释放及其对一般村民参与感的促动, 使得这一时期L村敬老、养老、助老的信仰纽带不断巩固和强化, 西门宫的养老参与逐渐由单一性转向多元性, 单向性转向互助性, 临时性转向常规性、动态性;老年人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进一步得以彰显, 养老体验愈加真切可感。
3. 规范性和规模性:近十年来政府介入引导下的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
近十余年来, 老年人权益保护和农村养老助老事业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空前的重视, 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 明确“农村社区都要建立 (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集中就餐、托养、健康、休闲等服务, 上门为居家老人提供照护服务, 开展老年人信息登记、身体状况评估”等, 满足“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健康服务、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1) 。同时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坐落区位、建设规模、功能区设置以及服务内容与方式、运行管理与资金保障等作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 各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建设一时间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并“因地制宜”探索尝试了多种样式 (2) 。作为地处所属街道核心区的L村 (3) , 成立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并备受关注。依托西门宫成立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设想很快成为村里老人们的共识, “但 (征求意见时) 几次提起, 几次被 (街道、社区) 推掉了”, “主要是大家心理还有‘顾虑’”。但在村里老人的坚持下和宫庙管理小组的努力下, 最终遂了老人们的愿。
在当地街道、社区的支持下, 西门宫将730余平方米辅助用房整体作为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进一步完善了“生活照料”“健康服务”“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功能区的划分。爱心食堂、日间照料室、康复室、医疗保健室、图书报刊室、电子阅览室等一应俱全, 较好地满足了L村及周边村落老年人的日常养老照料服务需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与老年人日常照料服务中心的结合, 形成了当下L村西门宫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格局, 一套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宫庙建设与参与养老服务机制渐趋成型 (4) , 也成了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 (见表1) 。
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也表明, “发挥民间信仰场所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社区服务平台, 不断借力社会信众力量, (有利于) 促进民间信仰场所活动与社区建设的融合并进” (5) 。同时, 基层政府的介入引导, 实际上也是对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的认可, 使西门宫的养老参与实践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正名”, 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基层政府、社区和宫庙场所的和谐互动, 增进了民间信仰价值的社会认同, 激发了信众参与地方社会服务和融入主流社会、弘扬主流价值的主动性、自觉性。
(三) 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当代发展的实现机制
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并不是一厢情愿的简单过程, 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相对分立及相互作用。历史事实表明, “在总体性社会的国家垄断、支配绝大部分社会资源, 无神论意识形态被教条化的框架背景下, 无论是一般社会的慈善表达还是宗教领域的慈善表达, 常常是无源之水或可能被政治误读而搁浅。” (6) 纵观L村西门宫养老参与实践的历史形态, 尤其是在当代乡村社会变迁中逐步走向社会化、常态化、正规化、优质化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正好是国家推进与宗教关系、市场关系、社会关系、个人关系的制度规则在变革中逐步确立优化的过程, 是社会 (个人) 物质基础不断增强与丰厚的过程, 也是社会公共领域互信、互助、互利结构相关因素不断生成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传统民间信仰是乡村社会重要的子系统, 其场所及活动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格外引人关注, 养老参与的方式、途径、领域及实现程度往往与社会认知、政府定位、市场发育、场所状况以及其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力等紧密相关。
1. 政教关系的调适: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制度前提
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及其发展, 就其内部来看, 有特有的宗教情怀的激励和传统道德文化的感召, 在此种因素相对稳定并持续滋生的情况下, 外部的制度环境———国家与宗教关系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政教关系也各有不同的模式及实践类型, “但政教分离是许多国家在处理政教关系上的价值取向” (6) 。当然, 政教分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实践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我国, 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摸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 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并转化成为制度性或法律性成果, 包括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坚持各宗教平等、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以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 国家与宗教的分立与协作关系得以巩固实施, 使中国宗教和宗教社会慈善迅速恢复, 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健康有序的发展态势。国家与宗教关系的积极调适, 为传统民间信仰迅速回归乡村社会提供了制度空间, 并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中不断衍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开始积极回应, 促进了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新生。同时, 与迅速兴起的宗教慈善以及政府救助等形成关照呼应、交融叠加, 从整体上共同增进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比如, 近十余年来, L村西门宫的养老参与多次得到上级领导肯定并获得各级各类先进荣誉 (7) , 说明“国家在场”作为过去的控制力量已渐渐转变成为助推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 坚持宗教法治方向, 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原则框架下, 政府积极调适自身与宗教的关系, 尊重和引导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 信仰资本的集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可靠保障
民间信仰养老参与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的慈善行为, 若要得以持久地实现, 离不开慈善资源的有效供给, 既包括人力、金钱、实物产品、奉献的时间等以社会财富积累为前提的物质特性的资源, 也包括慈善行为、场所及相关组织的声誉等可以召唤民众对其养老参与给予关注和认同的符号性慈善资源 (1) 。民间信仰的主要阵地在农村, 信众主体是农民, 长久根植于地方社会, 拥有代代相袭的道德文化传统和难以计数的信众, 这也构成了其最重要的资本———信任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 又因“信仰”之联结, 使其内含着较强的宗教软约束力和社会动员协作力。正因这些资本因素的集聚, 使民间信仰体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一旦遇到新鲜的空气和制度的空间, 它就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而生机勃发, 越来越多的民众身体力行投入庙宇建设、信仰活动和积善成德的各类社会服务包括养老服务中来。因此, L村西门宫在历次重修扩建中短短几日就能迅速募集数万、数十万或数百万计的善款;长期参与宫庙轮流值守或直接参与养老服务的信众义工达120余人;善款收入年年有结余 (2) 。从善款构成看, 70%以上来自于神灵寿诞、圣诞和春节庙会活动的乐助捐资, 20%以上来自日常的香烛和“元宝”销售收入, 约10%左右来自宫庙“功德箱”收入。善款除用于日常的宫庙维护、群体性仪式活动支出, 约有80%左右用于补助老人、资助贫困以及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换言之, 西门宫养老参与的经费几乎全部依赖于信众, 西门宫养老参与的志愿服务者几乎全部来源于信众。
若没有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对L村民众创造力的激活, 没有市场经济为L村民众提供财富积累的巨大空间以及其对个体自由的促进, 没有社会层面的敬老护老道德文化的不断唤醒、传承和慈善意识的提升, 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以及L村民众对信仰场所形象、声誉的维护, L村西门宫养老参与的新发展也将无从谈起。因此, 对于民间信仰养老参与而言, 维持其恒久的动力, 需要弘扬“崇德敬祖”信仰文化精神, 突出规范引领和服务社会导向, 不断增进信众认可、社会认同, 才能不断整合集聚养老参与社会资源, 推进养老参与社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化, 更好体现“信仰资本”独特的集聚效应和社会价值。同时, 也为传统民间信仰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型和村庙管理组织建设优化了外部环境。
3. 社会政策的“溢出”: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潜在动能
改革开放后,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策调整以及对宗教慈善的引导和鼓励, 拓展了宗教与政府、社会、市场的互动空间, 各类宗教慈善活动快速兴起、专门的宗教慈善组织也在各地渐次出现。在此背景下, 民间信仰与地方政府、基层社会的关系也逐步呈现出新的格局, 即由过去政府视民间信仰为教育转化的改造对象, 主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的方式加以严厉控制, 逐步转变为政府面向的社会事务而加以积极引导和管理 (3) 。这实际上意味着民间信仰已经从过往与主流文化相异而处于相对封闭领域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 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交往互动的障碍逐步得到排除。在广大信众看来, 这些都预示着民间信仰养老参与将可能获得更大的政策空间和社会空间。
因民间信仰较之于制度化宗教更具灵活性、本土性以及可脱敏性, 与地域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 与地方政府官员也有着密切的历史相关性或家庭相关性, 一直存在着微妙的情感联结, 一旦出现社会政策的空间, 民间信仰养老参与赖以存在的各类显性、隐性资本或将加速集聚。加之民间信仰属性的多元性、模糊性, 极易受到宗教、文化、经济和乡村社会公共服务诸领域利好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 既常常游走于政策边缘, 也可兼收共享诸领域的政策利好, 或择优而选。这些既共同构成了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存在状态, 更成了民间信仰养老参与巨大的潜在动能。
4. 主流价值的彰显: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认同是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是增进社会认同的重要条件, 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撑。相较于一般性的社会慈善养老或宗教慈善养老, 民间信仰养老参与极具特殊性, 常游走于政策边缘或难以展开, 信众的养老慈善愿望和实际行动也时常被遮蔽, 其根本原因集中体现于当下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特殊生存状态———文化合理性凸显与身份合法性缺失的尴尬。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由草根文化逐步被推向地域精神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而进入国家主流话语体系。在民间信仰场所及信仰活动中, 时常可见国家符号的张扬或国家诸要素的实际在场, 集草根之智慧极力贴近主流话语、彰显主流价值, 表达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这一系列过程和努力, 实际上也是民间信仰不断扩大社会认同、增进社会共识的过程, 更试图为民间信仰的合法性追求添加助力。不难发现, 通过“国家符号”的不断植入来提升民间信仰场所及群体性仪式活动的声威已成为当下村落建设中的一种有效选择, 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对国家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的征用, 进而使场所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诸事项获得“合法性”依据 (1) 。
L村西门宫养老参与的新进展与其合法性的不断获得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一是努力找寻宫庙信仰的宗教“源头”, 依附制度化宗教, 于2002年被当地宗教部门批准为道教活动场所, 为其开展养老参与提供了身份的合法性。二是主动贴近主流话语, 以“喜迎奥运、欢庆盛世”等为主题, 高扬主流价值, 大规模开展庙会活动, 彰显宫庙信仰之于地域社会的意义, 不断积累扩建场所和改善设施的社会资源 (2) , 为其拓展养老参与提供了条件的合理性。三是忧基层政府之所忧, 乐乡村民众之所乐, 积极寻求政府认可, 与社区共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为其全面推进养老参与提供了理由的“正当性”。
三、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当代意义及政策取向
“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问题更为严峻。近年来, 各地采取政策引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助、农村自办、老人自治等方式探索尝试了多种互助养老方式, 有的初尝既止, 有的仅止于“吃饱”而已。推进农村老年问题的解决, 既要关心其物质层面的问题, 更应聚焦其精神匮乏问题, 必须立足农村社会实际, 尊重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主体性, 通过优化整合各类资源, 构建乡村熟人社会“互助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 使老年人在友爱互助的宽松环境中实现自助 (3) 。以L村西门宫为代表的部分农村社区实践的“民间信仰场所+养老照料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的老年照护模式, 较好地体现了“自助型”与“互助式”养老方式相结合的特点, 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老年人的主体自觉性和自身潜力, 逐步从传统的“被赡养”者的消极情绪中摆脱出来, 不断积累起自助、互助养老的的正向情绪, 初步实现了农村老人心养、身养、学养的三位一体。L村西门宫的养老参与实践也表明, 中国乡村传统信仰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与农村老年社会建设有其内在的联系机制, 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 既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 积极促进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 也可为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的转型提供路径指引。
显然, 相较于宗教组织及其它社会组织的慈善养老参与, 一村一庙的公益慈善显然“身单力薄”, 而且形制相对粗糙简单。但是, 不能忽视它的独特优势和内生活力:比如, 根植于地方的便利性与自助性、信众群体广泛的互构性与互惠性、形式灵活多样的可参与性与直接有效性、地方民俗传统的可接受性与可持续性等, 使所施之“善”可让施善之人更加“可知可感、可亲可近”, 并直接作用于乡风文明, 积极影响良善家风、村风建设。在国家倡导复兴传统文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以及乡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的背景下, 应该继续本着立足乡村社会实际和群众需求导向, 按“创新转化、开放包容、形成合力”的要求, 全面深入探索推进和规范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政策路径。
首先, 从国家层面来看, 应辩证看待民间信仰的社会作用, 推动形成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正确舆论导向和制度环境。由于民间信仰的宗教性和原始性特征, 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参与方面还存在诸多没有完全脱敏的领域, 而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却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共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宗教与文化治理体系的日臻成熟, 民间信仰的意识形态障碍逐步被破除, 为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留下了空间。但是, 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民间信仰自身的局限性, 加之长期受压抑而突然释放所衍生出的诸多怪象, 客观、理性认识和对待民间信仰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都还远未形成, 民间信仰参与农村养老服务还处于局部的尝试性摸索中, 面临着理念上、制度上和具体操作上的困惑。比如, 有的地方一些部门对民间信仰的长期存在和民众的实际需求或视而不见、或常怀警戒之心, 更有一些“主流人士”对民间信仰及其信众常持鄙夷心态, 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实践甚至被看作是搞封建迷信。
助老扶弱、服务社会是民间信仰最重要的正向功能之一, 它的实现需要积极的社会认知和良好的舆论环境。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正常的) 宗教信仰是改善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状况, 增加人们幸福美好感的重要社会途径”, “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最佳途径 (之一) ” (1) 。就民间信仰而言, 参与社会养老服务, 有其宗教性———“信仰”的驱动, 甚至带有一定的功利化和迷信化色彩。但着眼于乡村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 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在客观上起到了精神救济、扶危助困、聚合社会资源以及缓和城乡变迁中的巨大社会张力等作用, 并成为官方或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补充。因此,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过程中, 应恰当地对社会各群体加以引导, 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看待民间信仰及其养老参与实践的舆论环境;同时, 还应加强对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相关政策研究, 进一步明晰操作路径或政策取向, 积极创建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良好制度环境。
其次, 从民间信仰层面来看, 应以主流文化为引领, 以规范场所建设为基础, 推动形成健康积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场所环境。民间信仰养老参与最有优势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多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 其中村庙秩序和村庙管理组织的自身建设尤为关键, 并与一地一域的村风民风形成互动、互为前提, 共同作用于乡村社会的养老环境和养老事业。近30余年来, 中国民间信仰的快速恢复兴起, 最直接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庙宇的复兴。作为传统村落象征性建筑———庙宇的重建, 逐步实现了乡村民众曾经失落的生活本真的回归,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新时代的乡村带来了新的振奋和新的气息。同时, 庙宇的乱建、滥建, 迷信陋俗的复燃, 村庙管理的混乱以及据庙敛财、消防安全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健康有序的社会服务和养老参与自然无从谈起。因此,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给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留出政策空间的同时, 也不能放任自流, 要坚持保护合法、打击非法, 积极引导并采取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 避免民间信仰资源的滥用及其负面因素的无限滋长。
就民间信仰自身来说, 要努力将场所建设成地方性知识的展示窗口、地方传统文化和地域精神的传承基地、地方民间文化艺术的展演平台, 地方传统节日礼仪诠释的实践样本和敬老爱老护老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播扩散中心, 以及汇集乡贤智慧的主要阵地。此外, 民间信仰场所在开展养老服务中, 还应引导信众淡化信仰色彩, 突破区域性祭祀圈层限制, 突出服务质量、服务公平和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自觉加强场所规范性建设和保持自主性的基础上, 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 主动接轨社会政策框架, 努力与地方社会整体性的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共进。
第三, 从社会层面来看, 应倡导自主自愿和互助共享, 推动形成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社会协作网络和联结机制。动员民间力量来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而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中, 社会慈善福利和养老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事实证明, 在中国各地区, 政府包办型或主导型的养老服务在广大民众中有极高的信赖度和需求度, 但政府力量是极为有限的, 仅仅依凭政府主办养老事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显然力不从心。因此, 鼓励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是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重要文化资源, 或可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对于乡村社会的养老参与是促进自身转型和彰显当代意义的重要方面。但是, 民间信仰的养老参与是具有显而易见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的, 不可能独立支撑乡村社会的养老服务事业, 也难以成为乡村社会养老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或主要力量。毋庸置疑, 无视这种养老方式的存在合理性和存在意义, 或过度地放大这种养老方式的存在意义和拓展空间, 都是不恰当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乡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养老服务资源日渐充分, 但也还存在着配置不均衡、供需不对称和各种养老服务相关的社会力量自发分散、孤军作战等情况。因此, 加强对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村域内外各种社会资源和服务力量的有效整合、链接是非常必要的。在这当中, 基层党委政府应积极引导, 更加重视发挥好村落 (社区) 组织的中枢作用, 协调促进村庙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站 (室) 、老年协会以及其它相关民间慈善组织既保持各自优势, 又相互合作, 基于自主自愿、平等参与、互动共享的原则, 以及提升乡村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目标, 推动形成民间信仰养老参与的社会协作网络和联结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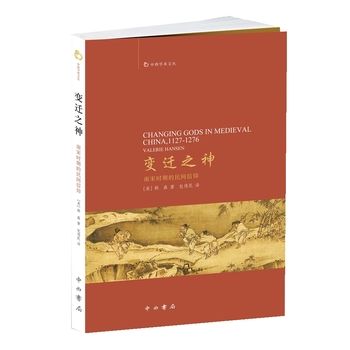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