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le Religion,Four Sacred Animals (Sidamen) and Grandma Wang:Rural Religion Studi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作 者:岳永逸
作者简介: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世界宗教研究》(京)2018年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诉求中,燕大社会学系始终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1930年代盛行的功能主义很快被燕大社会学的师生融入到了对其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诸多研究之中。在此潮流中,基于考现的平等交流和参与观察,摒弃了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的乡民信仰实践不再是“迷信”,而是宗教。在偏重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功能认知而对庙宇宗教和四大门宗教精彩的“热描”中,王奶奶成为活生生的人神、妙峰山红火的香火呈现出更清晰的纹理。作为社会制度的香头、家庭宗教的提出以及拜神求佛之“家务事”属性的发现,对全面深透的认知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也有着非凡的价值。
关 键 词:乡土宗教/庙宇/四大门/王奶奶/热描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平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1937-1949)”(14BZW153)阶段性成果。
一、功能论与燕大社会学系
1922年,主要由甘博(Sidney.D.Gamble)出资赞助,步济时(John.S.Burgess)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燕大)社会学系成立,①其开设的课程以及研究成果多与宗教相关,侧重服务于宗教。1918年9月起,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当时还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甘博和步济时受1914年美国“春田调查”(Springfield Survey)的影响,开展了对北京的调查,其成果即至今都意义非凡的《北京社会调查》。②因此,燕大社会学系初期的师生对社会调查并不陌生。1926年起,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开始改由中国学者担任。先后出任过该系主任的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诸人都有着留美的背景。这样,因为教会大学本身的特色、教职员工的构成与社会学的学科特色,燕大社会学系与欧美的同行始终有着密切的交流,或请进来,或走出去。在从许仕廉开始一以贯之的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诉求下,③燕大社会学不但始终与国际接轨、力求同步,民俗研究在燕大社会学也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其十大研究之首。④
1932年秋天,许仕廉迎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Robert.E.Park)来燕大讲学。派克将其以研究美国都市为主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系统介绍到了中国。派克的到来和现身说法,将作为时空单元,也是研究者可观察的“社区”(community)意识,注入到了费孝通等年轻聆听者的学术生命之中。⑤1935年10月,燕大社会学系迎来了当时翘首世界的功能主义大师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燕大讲学一个半月的布朗,系统地介绍了其偏重于初民社会研究的功能论与比较社会学。作为当时在欧美学界势头正旺、影响正盛的社会人类学流派,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对功能论表现出了师法的热望。1936年,燕大社会学主办的《社会学界》第九卷就是“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该辑刊载了布朗的《社会科学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原始法律》诸文中文译文的同时,也刊发了吴文藻写的导论式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杨开道《布郎教授的安达曼岛人研究》、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等诸多重量级文章。
在推介功能学派的过程中,用力最勤者非燕大社会学系时任主任吴文藻莫属。先后撰文介绍过法国、德国、美国等社会学研究诸多流派的吴文藻,在多方比较中最后选择了功能学派。他认为,实地研究的精神和实际应用价值兼具的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新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⑥这一认知,实际上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自我修正相吻合。在美国,以派克为代表的研究都市的人文区位学倡导的社区研究,虽然偏重量化,有着更多的统计分析,但文化与区位、人口一样,是人文区位学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与此迥异,殖民霸权色彩浓厚的初民社会研究始终都关注文化。在功能主义这里,文化是各种制度互动形成的整体,对这些制度的配置与使用即功能。这样,都关注文化的社区研究与功能研究在吴文藻、赵承信、杨堃等中国学者这里,殊途同归。1938年,费孝通、贾元荑、黄迪三人翻译的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的《文化论》在《社会学界》第十卷刊发。为了人们更好的理解马氏的文化功能主义,紧随费孝通等人的译文之后,吴文藻刊发了其长文——《文化表格说明》。
1938年,时任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开始张罗、主导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的研究。之所以命名为“社会学实验室”,而不再像此前的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区那样称为“试验区”,是因为在经过对社区研究和功能论的学习消化后,赵承信等人明确将调查范围限定在调研者可以进行全方位整体观察的“小社区”。距离燕大不到半个小时脚程、人口不足三百人的平郊村⑦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尤其是,建设中国化社会学意念的延续与进一步强化,使得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们不仅重视经验事实的获得,同时也将调研者如何在平郊村展开研究纳入观察的范围。⑧这样,因为要将服务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调查”提升为带有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并对叙述的事实进行比较、解释说明的“社会学调查”,⑨再加之时局动荡,不得不终止的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区反而递进为了平郊村这一精致的社会学实验室,以此服务于中国化社会学之认知论与方法论的建设。
因为功能学派原本就与以涂尔干(

二、局内观察的考现
与同期的海淀阮村、冉村一样,(14)平郊村这个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郊村落,是个“城乡连续体”。因为与燕大和清华大学比邻,并长期作为两校师生的观察以及实验基地,平郊村在城乡之间、都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的边际性、过渡性更加明显。一方面,它保持着乡村固有的家庭组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都市经济以及西洋文化、战争的影响,从而过着两种生活。正因为如此,指导本科学生在平郊村采用局内观察法进行社区研究与功能研究的赵承信、黄迪与林耀华,更为关注平郊村的人口、政治组织、鸭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医疗、家族等形态与城市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尝试呈现其社会组织、经济形态、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特征等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混融性。(15)与上述几位稍有不同,1937-1941年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杨堃所指导的毕业论文,更关注在平郊村这个“时空连续体”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岁时节日与宗教日常。
那么,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将人文区位学的都市社区研究和比较社会学之初民社区的功能研究综合运用,并进行“一种方法的试验”呢?赵承信曾总结道,研究者自己下乡的详细记录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言行互动的记录,都是方法论的题材。试验研究法就是“在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记录活动则是“为控制试验的初步工作”。(16)平郊村研究是在1939年暑期开始的,所以是教师和学生一同下乡,每星期四至五次,每次都由燕大社会学系在平郊村的主要合作者、向导,时任的平郊村小学校长H君带领,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之后,下乡次数相对减少。大四学生因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每星期至少下乡一次。同期,教师约每月下乡一次,以联络村民和指导学生。寒假期间,大四学生就搬到村里居住,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日常中进行调研。大四学生毕业了,大三时选修过社会研究法课程而接触平郊村民的学生顶替上来,继续研究。(17)
作为平郊村研究的亲力亲为者,杨堃也曾有所总结,并强调这些基于田野作业所获取的材料与可能有的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关于实际研究的方法,我们全是采用民族学家调查初民社区的方法,亲人农村,与农夫结为朋友,过着农夫们的生活。从自身的体验与观察之中,以取得实际的资料。大部分的论文,全是这样得来的实际的报告。文献的资料,仅是供参考与比较而已。”(18)对于此前基本没有记录与研究,抑或被各色精英武断地视为“迷信”的四大门宗教,李慰祖更是只能采取局内观察法,探查其详,穷究其理。
为了展开调查,李慰祖先行学习了平郊村一带乡民的土语,尤其是四大门宗教中的“行话”。在展开调查时,他竭力避免自己局限于一两个人提供的信息,尽量与更多的人直接交谈,以获取广泛而全面的信息。对于香头的内部知识,即“秘密的部分”,如同黄华节(黄石)早些年所倡导和实践的那样,(19)作为“忠实的信徒”,李慰祖亲自去不同的香坛求香。为此,他曾到老公坟王香头、南长街土地庙二号王香头、清河镇东南的仓营村开香头等香头的香坛,为祖母求香;到西柳村王香头香坛为舅母求香;陪同学高郁武等到海淀碓房居刘香头香坛求香。因为这些实践,李慰祖与众多香头形成了良性互动,获得了香头们的认同。(20)这种亲力亲为的“以身试法”,迥然有别于16年前顾颉刚等人调查妙峰山时,“假充了朝山的香客”,(21)只动眼动手,却不置一词的“闷葫芦”式默不做声的旁观笔录。
就自己如何有效获取香头群体的内部知识,李慰祖写道:
关于“秘密的部分”,作者便由十几个香头得到所希望的材料。作者到“香坛”去“求香”,向他们表示同情,对于“仙家”奉献供品。无论如何,已然多少具备一个信徒的条件了。由于气味相投,他们便会很高兴的叙述“当差的”历史,拜师的典礼,“朝顶进香”的盛况,仙家显着的灵验等等。这些材料都是香头的专利,而为一般乡民所不知道的。(22)
当然,即使是作为香客与香头交际互动,因为怕引起香头的反感,从而有碍参与观察的顺利进行,李慰祖还是忍痛割爱地放弃了用照相方式对香坛布置、香头下神仪式的记述。换言之,在田野现场,观念和方法论意识都明确的李慰祖,已经游刃有余地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得以完成对四大门宗教的清楚呈现,其著述也最终成为被后人频频征引的经典之作。
在调查平郊村的庙宇宗教时,陈永龄既有常常数小时的访谈后一无所获的苦恼,也有对于参与观察重要性的真切体悟。他指出:研究宗教信仰,如果不能与村民朝夕相处,就无法体察村民的信仰,因为这些信仰“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只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心领神会,潜移默化,才能得知他们内在信仰的真实性质”。由于自认为没有达到“默会”的这一理想状态,陈永龄实事求是地将其研究定格在了“实地研究工作初步尝试的结果”,是“以后做专门学问的一个起始”。(23)当然,在调查中,为获得合作者的认同,尤其是与之建立起互信的“朋友”关系,也有人将在中国社会人们惯用的烟酒派上了用场,从而使田野工作顺利展开。(24)
三、乡土宗教的功能、阶序与系谱
主要通过作为人神之媒的香头顶香治病或瞧香治病而呈现的四大门宗教,长期在北中国盛行,还经常是一个庙宇香火红火的本质所在,北京城乡也不例外。至今,主流话语大抵依旧将香头和在神像面前的烧香磕头等敬拜实践,定格为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而同步建构出来的“迷信”(superstition)。(25)因此,在清末以来的反迷信整体语境中,作为庙会的中坚,香头与香客在神祇前的顶礼膜拜、许愿还愿始终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是要公开禁止甚或高调打压的对象。(26)自然而然,在琳琅满目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名录中,不但香头缺位,冠之以庙会头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常也是被归在民俗类抑或表演类,公开用语词擦拭、遮蔽其宗教实质。于是,在当下的华北乡野,以香头为核心且处处花开的“家中过会”(27)在媒介是缺失的,在学界基本上还是一种匿名的状态,少有人关注、叙写。
然而,80年前,在社区研究和功能研究引领下的平郊乡土宗教研究中,涂尔干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认知论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无论是偏重于平郊村庙宇敬拜的陈永龄,还是专攻四大门的李慰祖,对于乡民的这些敬拜行为,二人都直接以“宗教”称之:或者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言其有别于世俗(profane)的神圣(sacred)的一面,或者将之视为对社会生活需要的回应,因需要而生,有着种种功能。
在其《文化论》中,马林诺夫斯基将宗教定义为:“宗教是和人类基本的,即生物的,需要有内在的,虽为间接的,联系。好像巫术一样,它的祸根是在于人类的预测和想象,当人类一脱离兽性,它便开始萌芽。……宗教并非产生于玄想,更非产生于幻觉或妄解,而是出于人类计划与现实的冲突,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混乱。假如人类没有足以保持完整和供为领导的某种信仰的话,这种冲突和混乱势必发生。”(28)这个大致基于单线进化论的宗教功能主义认知被陈永龄引用,作为其定义、研究和分析平郊村庙宇宗教的基本指针,以致于他将马氏的理性表达进行了更为浅白的译写:
人类在其重要生命转机的时候——如生、老、病、死的关头,情绪及精神上都有急骤的扰乱与变化。这样常常造成一个人的人格解组;大而言之,也易造成社会的紊乱。因为在这个危难的关头,人类的智慧、经验、知识,已是没有用武之地,既然在人的方面找不着出路,所以便把信念与希望转升而为对超自然及超人的崇拜,因而保持了自己身心的调整平衡,积极的来应付这当前危难的关头,这也就是宗教生活的发生。(29)
进而,在其研究中,陈永龄将熏染中国人的“庙宇崇拜”和“家庭祖先崇拜”并列,将平郊村民主要围绕在村西北角的延年寺之宗教实践直接以“庙宇宗教”称之,认为“庙宇宗教在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有着其“特殊的功能”。(30)然而,他感兴趣与研究的并不是“庙宇宗教本身”,而是“庙宇宗教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功能,作用”,即关注的是庙宇宗教和村民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明确宣称自己用的是“社会学的观点”,而非“宗教学的观点”,并专章描述讨论延年寺之于村民生活的宗教、教育、政治、经济、社会和娱乐等诸种功能。(31)
同样以“宗教”冠名四大门的李慰祖,“绝难以同意”加诸给“求香者”头上的“迷信”一词,因为“这个模糊的词字非但不足以增加我们的了解,反之适足以成为研究的阻碍”。(32)因此,他采用比较宗教的研究,抛弃先入为主的任何障碍物和所谓的信仰的真伪,直面事实真相,以求“描述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并且企图在事实中能以寻出这种四大门宗教对于农民生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33)引用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观点,李慰祖将四大门宗教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的反应”,强调“其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并点名批判荷兰人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美人明恩傅(Arther H.Smith)和法人禄是遒(Henri Dore)等西人对中国农村宗教的研究态度不但感情用事、充满了宗教的偏见,而且是距离事实太远的“非科学的”,对于“我们的研究并无多少补益”。(34)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是振聋发聩的独立的批判性认知,使李慰祖对于四大门宗教的定位更加客观,摆脱了单线进化论以及教化论、革命论的羁绊,更清楚地看到四大门对于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积极、合理的一面。
除已经提及的黄华节等极个别人的研究之外,在七八十年前中国学人的乡土宗教研究中,这种实证的取向,直接将民众之言行推向前台,并试图诠释乡土宗教发生的动因与其对于乡民生活不可缺失的功能,罕见而难得。尤其是长期立足于一个社区或边缘性群体,在系统而全面的调研的基础之上对乡土宗教进行叙述、比较与说明者更是寥若晨星。因始终“保持严明的社会学立场”,李慰祖在舍弃了对于香头“反常”行为——神灵附体而迷狂的心理学解释的同时,直接将其研究欲回答的问题归结为四大门宗教的性质与功能两个方面,功能方面又包括:“四大门信仰的功能是什么?香头在社区中负责什么任务?何以在‘破除迷信’的旗帜之下,香头制度在不利的环境之中,能够依然存在?”(35)从治病、除祟、指示疑难、调停、禳解、安楼等香头之于社区生活的功能,李慰祖都在力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通过香头集中呈现的四大门宗教的合理性。他还指出,在反迷信语境中,在警察对香头的盘查以及取缔之中,香头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且还出现了香头折服警察,后者为前者排忧解难的案例。(36)
正是基于长期的参与观察,在杨堃指导下的北平乡土宗教的民俗学志中,研究者们明确提出了乡土宗教的不同类型,即家庭宗教、庙宇宗教和四大门宗教,强调三者之间鼎立又相互补充的互惠关系,并力图结合信众的敬拜实践和主位认识,勾画出乡土宗教的神灵系谱及其阶序。简言之,家庭宗教,是发生在家居中的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拜。庙宇宗教,是在家门之外的庙宇这一公共性的社会空间对神灵的敬拜。四大门宗教,是跨越家门内外的,对胡、黄、白、柳四大灵异动物—仙家——四大门的敬拜实践,又有家仙和坛仙之别。普通人家在场院一角的“财神楼”供奉的家仙,旨在保佑家宅平安、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香头家供奉的坛仙则能看病看事儿与除祟。(37)在这些民俗学志中,村民、信众、神媒—香头直接出场,其音声、神情、脉搏与气息交织成了一个乡土宗教完整而明晰的感官世界。这又是怎样的一幅人文图景呢?
1936年,于鹤年开列过一张详尽的北平神马清单,并强调这些神马对于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神马谁在供奉、供奉在什么地方、何时供奉、怎样供奉,于鹤年并未有任何说明。(38)与此不同,在杨堃的指导下,只要涉及到敬拜实践,1939-1941年这三年燕大社会学系关于民俗的论文,都会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敬拜的对象、敬拜者、时间、地点、仪式的过程和相关的传说故事等。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通常都是将敬神和祭祖分而述之。敬神又分为家庭中的祭拜和庙宇中的祭拜,认为庙神高于家神,对于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更盛的四大门则单列。
与庙神始终为善不同,四大门喜怒无常,还可能作恶。因此,平郊村民有四大门是“神里头的小人”这样形象的说法,(39)而禁忌多多。在乡民的宗教观及其实践中,庙神无力解决四大门的事儿,四大门的事儿只能求顶仙、当香差的香头禳解。不但乡民有病或事儿时求助于香头,为了香火,不少庙宇中也供奉有四大门抑或成神的香头。因此,四大门不仅在村民家居中安家落户,还与庙宇宗教、朝山进香有着诸多关联,是乡土宗教神谱与敬拜实践中有机的一环。直至1949年,在平郊村,作为巫医的香头还与家神、庙神、星命家、扶乩者以及风水先生等一道,和中医、西医强有力地分食着疾病与病人。而且,四大门宗教在平郊村仍然有着相当的势力和信众,巫医的人数多于中医,地位也高于中医,西医就仅仅只有徐志明一人。村民有病时,会率先与仙家联系,请香头治病。(40)
在《北平年节风俗》中,权国英关于年节期间的祭祖意义与方式的描述,主要在强调慎终追远的文化意义和殷实之家可能有的仪礼。(41)或者是因为研究地域过大,权国英强调了祭祖的普遍性。在平郊村这个小社区,陈永龄注意到了村民对于神佛的崇拜远胜于对祖先的崇拜。(42)村中只有于念昭、杨则锦两家供有祖先神位,一般村民仅仅只是在婚事之后的二三日才带新娘去祖坟叩头拜祖,认祖和认祖坟,以示正式成为婆家的成员,获得新的身份。对三代以内祖先之生日和忌日的祭祀,也只在于、杨两家举行。这两家之所以供祖先神位并祭拜,原因是一家为书香门第,一家为村中首富。反之,普通村民在家庭中的祭拜更多的是与生产生活相关,诸如:祭财神以及财神楼,秋收时在场院的祭堆,为求保佑骡马等牲畜而在六月二十三祭祀水草马明王(马王爷),正月初八的顺星,等等。简言之,以平实的记述,陈永龄不无尖锐地指出了将中国人祖先崇拜均质化的认知误区。即,在日常生活层面,体现并强化儒家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与乡绅关联更紧。将祖先崇拜视为中国社会抑或文化的特质,实际上是前仆后继的国内外的数代学者主观建构的结果,一叶障目之主观想象不言而喻。
在北平年节风俗的描述中,权国英基本上集合了她能搜集到的所有年节时人们在家内祭拜灶王爷的仪礼、言行与禁忌,并分述了年节时门神、全神、拜四方、财神和星神相关的祭拜言行。(43)既出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郊村,村民家中供奉最多的是财神和灶王爷,其次也有人家供奉指向平安和子嗣的菩萨、娘娘与张仙,以及只供仙家楼(财神楼)的人家。但村民真正信奉的财神,并非关公等文武财神,而是居住在财神楼中的仙家——四大门,尤其是“白爷”。平郊村村民不仅仅是在房舍中供奉财神楼子,在于念昭、全子修等村民的口碑中,延年寺同样是四大门出没、显灵的地方,而村正东一里多路的何家坟就是胡仙炼丹的大本营,“到了晚上,火球此生彼落,洋洋大观”,此外四大门的兴家败家、拿法某人的灵异故事、传说、稗话和人们找香头、坛仙求解的敬拜实践,皆有名有姓,时间、地点、人物、原委一应俱全。(44)
根据信奉神佛的程度,陈永龄将平郊村民分为了三类:完全信奉神佛的听天命者;半信半疑的听天命也尽人力者;完全信靠人力者。(45)三十多年后,基于其台湾乡村的经验研究,郝瑞(Steven Harrell)也对信众进行大致类似的划分:理智上依附于系统宗教理念,但行动上少有表现的理智型信仰者(intellectual believer);信奉所有宗教理念的真正信仰者(true believer);基于实用原则的行为上的信仰者(practical believer),即半信半疑者;忽视任何宗教可能的真实和有用性的无信仰者(non-believer)。(46)更为关键的是,陈永龄指出了这些不同程度的信仰者不仅对待疾病的态度不同,家居中神位的设置还有着分野:不设置神位者,无力设置神位者,只设灶王爷神位者,堂屋正中供奉有大佛龛者。(47)至今看来,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者而言,这些基于事实的分类,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于鹤年曾经列举的众多神马,在一座庙宇中究竟是如何排列组合的,相互之间是怎样的一种阶序关系,陈永龄浓描的延年寺有了清楚的交代。到1941年,平郊村延年寺结构简单。南北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是天王殿、香池、正殿菩萨殿和真武殿。东殿三间是娘娘殿,正对的西侧是1920年改为了简易小学的禅院。紧靠山门,天王殿东侧是药王殿和钟楼,西侧是五道庙。其中,因为治病延寿的药王庙和人死后报庙的五道庙分别指向生死,两个殿宇的进出之门在平郊村民的日常交流中就成了“生门”和“死门”。陈永龄不仅花费了整个论文七章中的三章,过半的篇幅,图文并茂地记述延年寺中诸多神灵的形制、区位与阶序,还大致结合文献记载和村民记忆,梳理了这些神灵的来龙去脉、神格及其功能,记录了口耳相传的灵应故事。在神话仪式学派的指引下,他认同先有宗教信仰,然后才产生了相关的解释文本,即种种传说和灵验故事,并强调这些赏罚分明的灵应故事促使村民向善、不越轨的道德性和柔性控制力。(48)
在对延年寺内庙神的神系进行了清楚的描述之后,结合其实地观察时平郊村的家庭敬拜、各庙殿的整洁程度、局部空间职能的变化和村民的主位表述,陈永龄指出了这众多庙神与村民的宗教实践之亲疏远近,以及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首先,庙宇宗教乃家庭宗教的补充,实为妇女的“家务事”,四门大宗教又弥补庙宇宗教之不足,三者共同构成了村民的宗教世界与体系;其次,庙神之重要性的决定因素不是所在正殿抑或偏殿的区位,抑或佛道二教的神灵阶序,而是村民理解的这些超自然存在的神格及其之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功能;第三,因为与妇女小孩关联紧密,在所有的庙神中,观音、子孙娘娘、眼光娘娘、天仙娘娘等女神最受村民亲近,是“最有地位的神佛”,偏殿娘娘殿的香火才是全寺之冠。第四,庙运与村运、国运紧密相连,大的社会之变明显影响着平郊村庙宇宗教的兴衰。原本作为传统习惯并偏重于仪式的庙宇宗教,日渐出现了神秘化少而社会化多、宗教信仰少而道德观念多的态势。最后,简易小学、第二分驻区公所以及合作社、互助社或长或短在延年寺中的设立,多少都弱化了延年寺之于村民宗教敬拜的职能,而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多元与异质的现代性色彩浓厚的公共空间。(49)
在家户内外、村庙和丫髻山、妙峰山等不同空间出入的四大门同样有着鲜明的差别与阶序。在财神楼供奉的家仙,是稍稍得道的四大门,仅能保佑家宅平安,不能安龛塑像。坛仙则道行高深,是在山中修炼,直接由“老娘娘”碧霞元君管辖,在家中有一套专门的典礼,为仙家之塑像或绘像安龛设坛。通常,保家坛的家仙不降坛、不开口说话,事主不当香差,只是每月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烧香敬拜。香坛的仙家必然降坛,香头也必须为之当香差,或瞧香治病,坛仙不附体,香头当“明白差”,或顶香治病,坛仙附体,香头当“糊涂差”。因此,坛仙须每日早、晚或早、午、晚三次烧香,在龛前供奉茶、酒、菜蔬、鲜果、饽饽和鸡蛋等。(50)
坛仙之间,又有着道行高下之别。因仙家与香头之间两位一体,坛仙之间的高低关系就表现为香头之间的师徒关系。当一个人被仙家“拿法”作祟折腾要其当香差时,请来的香头就会顶神与作祟者之间交流谈判。成功的话,作祟者-被拿法者成为请来的仙家—香头的徒弟,进而前者在后者的指导下,经过安炉、安龛(安坛)、开顶等系列“成人礼”之后,成为给仙家当香差的香头。香头的这些成人礼、相互之间参加收徒开坛典礼、丧礼,定期进香朝顶,(51)在进一步固化同门香头之间关系、明确相互之间的尊卑高低等差序关系的同时,也强化着一个师门香头与王(三)奶奶、老娘娘之间的链接,使一个香头既是一个师门的,也是一个社区的和一座圣山的,有了更多的社会链接与合理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香头的这些成人礼至今仍在华北乡野有条不紊地上演。(52)
在村民的神灵系谱中,坛仙,又较庙神低下一等。京郊丫髻山和妙峰山等庙宇中都供奉有的王奶奶,是四大门的总管,老娘娘又是王奶奶的上司。(53)为了获得同行的认可,一个香头不得不在师父的带领下前往丫髻山或妙峰山等地,例行性开顶,并以师门为单位,带领各自的善人年度性朝顶,从而保持与王奶奶和老娘娘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以得到后者的庇护和加持。仅以海淀杨家井十九号的张香头所在的四大门为例,他本门各香头及善男信女、治好的病人,每年要在不同时日前往各山寺朝顶,分别是:(1)三月十五,天台山;(2)三月十七,东岳庙;(3)三月二十八(小建)、二十九(大建),丫髻山;(4)四月初六,妙峰山;(5)五月初一,通州李二寺;(6)八月二十,潭柘寺。(54)这样,四大门宗教自然而然被整合进了庙宇宗教体系之中。反之,通过众多不同门派香头及其徒子徒孙与善人,四大门敬拜在相当意义上影响了一个庙宇香火的兴衰。
不仅如此,四大门仙家还直接现身说法,以其灵验,为一个庙宇催香火,从而使该庙的香火猛然兴旺起来。清末时北京城灯市口东口的二郎庙一度香火的兴旺和1930年代北平西边八里庄佛塔香火猛然的灵验,都是因为四大门的入住。关于后者,后来还形成了俗语,“八里庄的塔,先灵后不灵”。(55)李慰祖早年的这些观察和记述,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20世纪末,潜在的胡仙使庙宇香火红火,却是光明正大的佛祖应着盛名,仍然出现在陕北。(56)
与此同时,在一个香坛,香头常常将佛、神、仙并置,将庙神反向纳入四大门的敬拜体系中,哪怕是这些神、佛居旁位,也不降神附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涵盖关系。与同期多数香坛都是将老娘娘、王奶奶同龛供奉不同,海淀碓房居六号的刘香头香坛有大佛龛三个,正中佛龛供奉的是玉皇、右边佛龛是观音,左边佛龛是药王。(57)此时,香坛已经如同一个缩微版的庙宇了。
四、冷描与热描:人神王奶奶
要充分理解这些基于功能主义对乡土宗教研究的意义,就不得不简要回顾此前的关于妙峰山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在京郊沿袭数百年的信仰圣地,妙峰山一直有着金勋、奉宽那样的人在默默地关注并记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朝山进香的满族人奉宽,在持续近三十年的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对妙峰山进行了一丝不苟地记述和考证。(58)见到此书稿的顾颉刚,先是惊奇,继而佩服、汗颜,并由衷赞叹,力促其正式出版。作为朝山者中一员的奉宽,除记述香会朝山的基本情形外,相当一部分精力都在记述香道沿途的风物、地名、金石等。人们为何朝山,为何要敬拜老娘娘,香会究竟怎么组织起来,朝山敬拜与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并不是奉宽试图回答的问题。此时,奉宽这个“局内人”反而更多的是跳出来的“局外人”,乃他者。
将妙峰山声势浩大的敬拜实践带入精英视界,并鼓动知识精英探究的则是1925年顾颉刚一行5人的妙峰山调查及其成果,《妙峰山》。(59)作为学界对妙峰山调查的开创性成果,顾颉刚等人的调查实则是旁观式的、游客式的。这些有着开创精神并敢于丢下书本的学人更多的是将自己看到的会贴等文字抄录下来,却疏于和香客平等的交流。如此,妙峰山敬拜依旧是平面的、被观看的,并将之移植到了香客、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在看到奉宽的著述之后,顾颉刚对之“正式的调查”“这才是调查的形式”等赞美,主要是针对奉宽所录材料的详实度:“几十字的固然不缺,几百字的也不加刊删;一件东西的行格、尺寸、地位,记得一丝不苟。”(60)
作为有着平民精神、革命意识的历史学家,(61)妙峰山香会始终在顾颉刚的学术帝国中有着位置,并尝试深入研究。根据《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和第三卷可知,从1929年到1937年他在燕大任教的9年期间,不管有无经费支持,只要有可能,他就前往,共计在庙会期间再上妙峰山六次,只有1930、1931、1935三年未曾前往。1929年5月17日(四月初九)至19日,回到北平的顾颉刚又张罗组织了人均花费9.24元的自费“一八妙峰进香调查团”,除在现场与众人商定调查及写作题目,事后还审读了周振鹤写就的《王三奶奶》一文。(62)这次调查的成果是同年7月《民俗》69-70期合刊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客观而言,无论是偏重于文献的罗香林对碧霞元君的研究,还是偏重于田野的周振鹤的王奶奶研究,都详尽了很多。除了感受、观察,调查者也有了与香客、会首之间的访谈交流,并且在18日归程时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北京同祀老娘娘的“三山五顶”(63)之一的天台山。然而,依旧关注香会的顾颉刚因为往返两日“未逢一香会”,在感慨“北平之衰落”的同时,(64)也根据他四年前的经验对妙峰山敬拜做出了“垂尽的余焰”之判断:“大约这种风俗,一因生计的艰难,再因民智的开通,快要消灭了”。(65)1933年4月29日(四月初五)到5月1日,顾颉刚与叔父顾廷龙、潘由笙一道上妙峰山。(66)此次调查,只有顾廷龙写出了一篇报告的上半部分来。(67)不知何故,除在日记中有所呈现外,1929年后的6次调查,顾颉刚本人都未再就他感兴趣的妙峰山写出文章来。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而且是只有为期两三天的调查,但即使放在当下,1925和1929年两次有顾颉刚参与、指导的调查成果都是丰硕的,而且是里程碑式的。如果正视包括妙峰山在内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诸多以敬拜为核心并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庙会在21世纪依旧红红火火的事实,那么顾颉刚当初“快要消灭了”这一似乎理性的预言与期望,明显是落空了。为何数次前往妙峰山且睿智的顾颉刚会对朝山进香这些乡土宗教出现误判?其根本原因或者是他只顺应了自己的逻辑以及学术兴趣,而始终都试图教育、唤醒民众的俯视姿态与革命心性。(68)换言之,虽然他率先走向了妙峰山,走向了香会、香客,但他并未能真正与之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朋友,其蜻蜓点水式短时间在妙峰山上下摇曳的身影,事实上依旧游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
以此观之,无论是从民俗学史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乡土宗教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采用局内观察法,真正与乡民、香客结成朋友的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对乡土宗教的功能论研究就意义非凡。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不再先入为主地将乡民的宗教视为是需要改造的“迷信”,而是成为了研究者自己的,研究者不再是冷漠的他者,而是热乎亲切的局内人。尤其是对于京畿一带人神王奶奶的敬拜而言,因为李慰祖、陈永龄的努力,此前被研究者看到的王奶奶成为了香头的与信众的,研究者之客位的王奶奶变为了信奉者主位的王奶奶。李慰祖的四大门研究更是史无前例地全面而忠实的记述了北平郊区以王奶奶、老娘娘为上级神灵的四大门宗教的内部知识,并揭示了其之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内价值”。(69)
传闻,王奶奶,是京东人氏,亦说天津人或天津三河人。她本是位老娘娘虔诚的信徒,因修行而成神。每月初一、十五,她都前往金顶妙峰山上香。平时,她为人扎针、瞧香治病,无不奇效,远近闻名,生前就被信者视之为神。在奉宽的记述中,金顶上王奶奶殿中的王奶奶,“塐村媪像,着蓝布衣,缠足,神采如生。天津人奉之极虔,称为王三奶奶”,并认为其是《汉书》所载之媪神,富媪,之遗韵。(70)同时,奉宽也提到王奶奶是妙峰山香道上最早创立茶棚之人的说法。在朝顶中道之关帝庙东南隅,有善人给王奶奶修建的墓地。墓前小碣正中题写有“王奶奶之墓”,左行题“创化施主,建立茶棚”,右行题“同治十二年孟夏,敬善长春众等重修”。(71)根据周振鹤1929年的调查,至晚在民国四年(1915),坐化后的王三奶奶已经享有了香火,信众为她在金顶妙峰山建起了小庙,塑上了神像。民国十二年(1923),善人在那时同样庙祀老娘娘的天台山为王奶奶修建了行宫。
或是因为王奶奶确实是三河人,或是为了强化王奶奶与天津地界的关系,天津香客格外崇信王奶奶。20世纪20年代妙峰山庙会期间,天津有数百个“带香会”。带香会或团体或个人,专门带人前往妙峰山进香。在庙会前,带香会在大街小巷张贴小黄报条,上书:“金顶妙峰山朝山进行,天仙圣母,王三奶奶,有香早送,由某日起,至某日止,送至某处。”有心而不能亲自朝山的,就到纸马香蜡铺买檀香木制的香牌,交付带香会。香牌上同样是将王三奶奶和天仙圣母并列。在天津天后宫的楼上,也供奉有王奶奶之神像,神像为身穿蓝布老式裤褂的七八十岁老妪。(72)
在通往妙峰山金顶不同香道的茶棚中,尤其天津人设立的茶棚中,王奶奶不是与老娘娘平起平坐,就是居于配殿,不少茶棚还配祀有四大门。在北道,天津同心堂设立的双龙岭茶棚正殿中,王奶奶与老娘娘、观音比肩而立;在大峰口施送馒头粥茶会,王奶奶与胡三太甲(胡仙)一道供奉在配殿;1932年,天津乐善社在磕头岭设立的茶棚会中,其配殿供奉着王奶奶;1934年,天津人张玉亭在苇子港/贵子港设立的茶棚中,王奶奶和大仙堂陪祀在正殿中的老娘娘两侧。(73)在中北道,响墙茶棚、青龙山朝阳院茶棚中,王奶奶同样陪祀在老娘娘旁边。响墙茶棚还有一个单独供奉老仙爷的小庙,仙门青龙司。青龙山朝阳院茶棚内还有柳十大仙静修、黄七大仙静悟、白二真人馨顺、柳四真人长真的神位。(74)
1925年,顾颉刚在妙峰山看到的王奶奶与同年天津天后宫中供奉的王奶奶样貌雷同,也是“青布的衫裤,喜雀窠的发髻,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75)仅仅4年后,周振鹤在妙峰山看见的王奶奶已非老妈子模样,而变为菩萨了:“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脸带笑容,肤色像晒透的南瓜蒂腹,红中带黄,盘膝坐。像高约五尺。”周振鹤也注意到,信众为了强调王奶奶由人成神的真实性,在王奶奶的塑像边还摆放了其真容:“用黄铜镂成的一座屏风式的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在丁卯年摄得的六寸半身的灵魂照片。”在王奶奶座下,还有两座高尺许的神位,上首是“南无三界救急普渡真君柳修因之仙位”,下首是“南无引乐圣母驾下胡二爷仙长之神位”。(76)在庙会现场,还有《妙峰仙山慈善圣母王奶奶平安真经》《灵感慈善引乐圣母历史真经》《慈善圣母王奶奶亲说在世之历史大略》和王奶奶的表牒、印章在传播、使用。不仅如此,几乎每个香会在灵感宫内老娘娘前上过表牒之后,就立即到王奶奶殿叩首焚表。换言之,此时的王奶奶在妙峰山不但与老娘娘分庭抗礼、争抢香火,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其实,不仅仅是善人、香客在散播着王奶奶的灵验,追封其为神圣,能够出入紫禁城中的各色人等、金顶的和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火热的“造神”运动之中,使得王奶奶与老娘娘平起平坐,甚或更灵验于老娘娘。在奉宽的记述中,光绪中叶,慈禧和光绪“二圣”曾经在颐和园遥观各路朝山之社火:“每山期逢驻园,则朝山各社火献技于此,两宫隔垣亲览焉。”同时,奉宽还提及慈禧为金顶灵感宫御书了“慈光普照”、“功侔富媪”、“泰云垂荫”三块匾额。(77)到1933年,在助善的江仲良以及是年77岁高龄的香会总管陈永立等人的口碑中,已经有了传闻中慈禧题写的“功侔富媪”牌匾是专门钦赐给王奶奶的说法。同年在金顶,以灵感宫主持僧宗镜的名义发散给香客的传单——“进香劝善歌接此一张带福还家”上的附录中有王奶奶灵验的故事。在这个传说中,王奶奶被说成是明末人,广施善行,清初在妙峰山坐化,乃肉胎仙,同时借民国初年其给天津刘姓香客显灵的故事,王奶奶与天津的渊源继续得以强化。(78)
遗憾的是,以奉宽、顾颉刚、燕归来簃主人等人为代表的记述,并没有揭示“活生生的人神”王奶奶在信众敬拜实践中“活生生”的一面,大抵停留在旁观者式的冷静素描——“冷描”,有着“游客之学”的共性。同样,因为少了四大门内部知识的踏查,不知四大门宗教乃“拟人的宗教”——四种神圣的动物前加以人的姓氏之特性,(79)周振鹤较为深入的观察、记述与讨论,也未能指出王奶奶与胡二爷、柳修因之间的关系,(80)同样止步于“冷描”。虽然陈永龄和李慰祖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少有参考奉宽、顾颉刚、周振鹤等前人的成果,研究也不是无可挑剔,且大抵有着比较和诠释相对浅薄等不足,却有了真正化身为信众中的一员,与之一同敬拜的热情和实践,从而带有温度和情感地“热描”出了四大门宗教的知识系谱,无意中厘清了四大门宗教与王奶奶敬拜、庙宇宗教、朝山进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简言之,该逻辑关联如下:在京畿之地信众的宗教学中,胡二爷-胡仙-狐狸和柳修因-柳仙-蛇(长虫)等四大门是王奶奶的下级。王奶奶又听命于老娘娘。香头不仅仅有着四大门上身附体的异态,还需要得到高居东大山(丫髻山)抑或西山(妙峰山)之金顶的王奶奶、老娘娘的认可,前往“开顶”,以此完成从边缘性附身(peripheral possession)到仪式性附身(ritual possession)的转型,(81)才有在家居内外的日常生活中服务于社区与信众的功能。为了保持其超自然能力,抑或“催功”,香头得年度例行性地在庙会期间前往丫髻山或妙峰山等圣地“朝顶”,将之与王奶奶、老娘娘之间的沟通交流常态化、制度化。(82)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前述的朝顶香道上同时供奉有王奶奶和老娘娘的众多茶棚。而且,如前文所述,以王奶奶为总管的四大门宗教影响到包括丫髻山、妙峰山等庙宇香火的兴旺,其在信众中的口碑、势力,甚或超过主神老娘娘。
在平郊村村民村外的庙宇宗教实践中,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庙会主要是宗教的,四月十一小口庙会和四月十八北顶庙会则主要是经济与市集交易的。在1940年前后,平郊村村民前往妙峰山朝拜的老年人会乘坐村里大户人家因许愿而还愿的大车,在妙峰山下住一晚,次日朝顶之后再回村。与此不同,部分青年人多会骑单车,当天往返。实在去不了的,也要在庙会期间,在自家的庭园中,对着妙峰山的方向,“顺一股香”,以示虔诚。同时,因为王奶奶和四大门的关系,平郊村与周边的东杨村七圣神祠、萧各庄地藏寺、六眼口增福庵、西杨村永安观之间有着亲疏不一的关系。
在平郊村西南数十步的东杨村七圣神祠,主祀关帝,但王奶奶的香火远胜关帝,远近村民都称呼此庙为“王奶奶庙”。该庙中的王奶奶与当年顾颉刚在妙峰山见到的王奶奶非常相近,是位身着蓝布衫,慈眉善目,手持旱烟袋,旁有拐杖的老妇人。塑像边,有村民还愿时奉献的三寸金莲。关于具体的敬拜情形,除提及平郊村的杨则锦家常有人来此烧香之外,陈永龄还列举了东杨村每天早晚到王奶奶殿敬拜的詹姓妇人和每逢初一、十五来此烧香叩头的东杨村张顺的母亲,并记述了她们坚持前往烧香敬拜的缘由。前者是因为四大门要詹姓妇人顶香当差,后者则是因为王奶奶指引应完官差后回家迷路的张顺平安到家。此外,距离平郊村一里地的六眼口村增福庵和距离平郊村约二里地的西杨村永安观,虽然主祀神都是关公,但在增福庵正殿西边的小屋,供奉着王奶奶,而永安观内则直接供有四大门的神龛。(83)
如果说研究平郊村庙宇宗教的陈永龄对王奶奶相关敬拜描述还是粗线条的远景,那么李慰祖则全面细致地“热描”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西北郊区王奶奶敬拜的全景,尤其是微观近景。西直门外大柳树村关香头在王奶奶下神附体时,道出了王奶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其口中,东山(丫髻山)王奶奶也是凡人成神的肉胎仙,其生前生活苦楚。在丈夫死后,她与傻儿子相依为命,最终在丫髻山铁瓦殿坐化。(84)与1929年妙峰山上的王奶奶已经凤冠霞帔呈菩萨状不同,1940年前后平郊香头家供奉的王奶奶仍是活生生而朴实可亲的人神,成老妪状,有着年画般的喜感:
在成府槐树街李香头“坛口”上,有东山王奶奶的塑像,是一个老妪的样子,端然正坐,头现佛光,白发参差,面皮上有皱纹,喜笑慈和,渥赭色的面孔,穿着黄色道袍,遍身全团花,座下列着一个“聚宝盆”,中间放着财宝。在王奶奶左肩之下,塑着一个农童,短衣秃袖而立,腰间系着褡包(束腰的带子),右手执着皮鞭,左手牵着一匹小黑驴。这是王奶奶的儿子,名字叫做“傻二哥”,又叫做“王哥哥”。……坛口上,还与王奶奶预备烟袋一份,菠菜绿的翡翠烟嘴,虎皮乌的烟杆,白铜烟锅,靑缎烟荷包,供在龛的旁边。……王奶奶下神的时候,便要吸关东烟,吸起来,烟便永不离口,并且要喝小叶茶(即较好的香片茶),喝完一碗,跟着又喝,有时喝的很多,并且有时饮酒,但是不用莱品佐酒,这都是王奶奶每次下神的惯例。(85)
在朝顶时,虽然是以王奶奶和老娘娘为上级神灵的这些香头在组织张罗,朝顶却已经成为这些香头的香坛所在社区的事情。善男信女,尤其是在香坛治好的病人,纷纷助钱、助力、助车,助香烛、香油、毛巾、毛掸等物。朝顶之前,人们还要在特定地点“开山”,以商议所有朝山事务,从而各司其职,分头行事。在此过程中,坛口是核心单位,进而形成了“朝山会”:
香头各“门”(系统)有各家的组织,结合的各团体,均都世代相传,团体的行动最重要的是进香朝顶。每个“坛口”是团体的单位,若干同门的“坛口”(从一师相传的坛口)组合而成为“会”,例如西直门丁香头便有“海灯会”,这个会朝顶的时候,以香油为主要的供品,刚秉庙李香头的会为“蜡会”,其供品以蜡烛为主,诸如此类,此外还有“清道会”以笤帚为主,“掸子会”以毛掸为主。海淀张斌香头本门的“会”创于清季乾隆二年,定名做“五顶长陞子孙老会”。会中有旗帜作为标记,旌旗存在张香头的师哥西直门外大柳树王奶奶坛上。因为后者在本门香头之中,辈数最大,所以同门共推她作为“把头”(会头)。这个会以“五顶”命名的缘故,是因为每年按期朝拜“五顶”。“五顶”便是天台山,丫髻山,妙峰山,李二寺,潭柘山的岫云寺。(86)
显然,在相当意义上,因为热描,李慰祖针对四大门香头的研究揭示出了奉宽、顾颉刚等人列举的百十挡妙峰山香会时不应忽略的部分“本相”。即,相当一部分朝顶的香会其实是以四大门宗教为支撑的。平郊村南半里地左右的肖家庄村民李瑞,曾经给西直门丁香头的海灯会到妙峰山进香助善。在募捐油钱之后,李瑞他们就在各捐户门前贴一张“香报子”。也即,曾经让顾颉刚痴迷的“香报子”有着两种来源:一种是香头所贴,一种是“朝顶善会”所贴。(87)这种来源上的差别,也是奉宽、顾颉刚所忽略了的。换言之,在当年具体而微的信仰实践中,正是因为与四大门之间的渊源,周振鹤所见的妙峰山王奶奶以及老娘娘的香火才如此兴旺。当年的周振鹤没有再进一步关注北京的四大门宗教,李慰祖也并未亲往妙峰山实地调查,其参考文献也未见提及周振鹤的《王三奶奶》。然而,正是这些前赴后继又各自为政的研究,才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20世纪前半叶,北京地区关于王奶奶以及老娘娘信仰的全貌。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吴效群等人又写出了可圈可点的关于妙峰山的民俗学志。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重新走向田野的研究,因为各自的出发点和理论关怀不同,在强化当下和听得到的“口述”历史的同时,差不多完全忽略了王奶奶曾经作为四大门宗教阶序神灵之一的社会事实。吴效群更是将王奶奶解读为天津香客用以与北京香客进行政治文化较量和宗教权力争夺的符码,并将王奶奶视为天津人的“碧霞元君娘娘”。(88)与有着重回田野而兴奋的吴效群在历史的迷障前的迟疑不同,在其精彩的胡仙研究中,偏重于文献诠释的康笑菲则将妙峰山的王奶奶编织到了北中国女神信仰与胡仙信仰的历史长河之中,大气磅礴。在列举了周振鹤、顾颉刚、李慰祖等人的记述后,康笑菲写道:“尽管资料之间存在差异,显然王奶奶的崇拜源自于民众关于胡仙的信仰,并且王奶奶本人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女性灵媒和其他边缘化女性的代表,这些女性灵媒和边缘化女性在当地社区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对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89)进而,康笑菲将北中国乡土宗教历史长河中的西王母、碧霞元君与王奶奶原本有着时间先后顺序的三位女神并置,看到了这三个女神的官方属性和个体特征不但代表了历时性升迁等级的不同阶段,而且也是同一种敬拜共时性兼有的不同面相。最终,康笑菲毫不吝啬地赋予了20世纪初叶才在京畿之地兴起的王奶奶这一“活生生”人神以巨大的文化内涵、价值理性与诗性。(90)
五、功能论对中国乡土宗教研究的推进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基本摒弃了“迷信”一词,但明确提出庙宇宗教的陈永龄并不决绝。按照经世济民、强国强民的功利主义视角、当时盛行的片面的科学观和对于民众教育、乡村改造等革命发展之逻辑,陈永龄在文尾将其浓描的庙宇宗教归结为了是百害而无一益,需要率先破除与改变的“消极、自私、出世的宗教”。(91)长时段观之,虽然明显有着作者自己也坦诚的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遗憾,但是功能主义引导下的以四大门宗教和庙宇宗教为主体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显然意义非凡。
首先,它尽可能摆脱了既有的“迷信”观,直面民众的敬拜实践。以“宗教”命名此前精英用“迷信”指代的社会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称贺的巨大进步。要提及的是,卢沟桥事变前,同样是在功能论影响下的燕大学生李有义在对山西徐沟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对徐沟的农民而言,宗教“不是信仰,乃是生活,不是空虚,乃是实在”,而且人们的整个生活都交织在宗教之中,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不受宗教的影响。(92)其次,研究者不但实地观察,还以身试法,与村民、香头、求香者成为了朋友。在相当意义上,实现了方法论的革新。第三,正是因为亲力亲为,调查不再是站在门外式的冷眼旁观或默观,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被对象化的他者,研究者自己与合作者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了观察、记录、分析的对象。与此同时,书写不再是一定要强调所谓客观真实的“冷描”,而是主观的、有着温度、烟火气息和情感的“热描”。惟其如此,才给我们保留了丰富而鲜活的七八十年前北平乡土宗教的实况,也才有了这里对当时的神灵谱系和王奶奶敬拜全貌勾勒的可能性。此外,还有数点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仙根”之说。(93)1948年,《四大门》被译为英文正式刊载,(94)新近也正式编辑出版了中文专书。(95)这使得四大门宗教广为人知,并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仍然少有人注意到李慰祖在其研究中记述并加以解释的仙根。如同当下华北乡土宗教中的“老根儿”,(96)仙根直接意味着人与四大门仙家之间可能有的亲统上的关系,即“人神”一体的同根同源性。不仅如此,仙家甚至还承载着“农民道德理想的结晶”。(97)通过为之当差的香头之间认师、安炉、安龛(安坛)、开顶等系列“成人礼”,通过相互之间参加收徒开坛典礼、丧礼和定期进香朝顶等典礼,胡、黄、白、柳四大门仙家之间的次第谱系在香头有着师门派别、堂号和字辈法名的师徒谱系图中清楚地展现了出来。尽管李慰祖仅仅绘制了海淀张香头门中的谱系图。(98)正是这些仙家与香头两位一体的师门谱系,精神世界中的虚拟网络,实化为现实生活中绵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二者相互影射,镜像叠生。这或者也是李慰祖直接在其论文第二编(上)“香头”之正题后加上了副题“社会制度”,并在结论部分直接称“香头制度”的原因之一。(99)
秉承林耀华的《义序宗族研究》《金翼》,许烺光的《祖荫下》,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已有研究,麻国庆继续强化着家、家族之于中国文化、社会结构举足轻重的地位。(100)确实,帝王崇拜强化的君臣政治伦理谱系、祖先崇拜强化的血缘亲情谱系、行业神崇拜强调的业缘师承谱系,从各自的层面,平行而交叉、叠合而混融地整合着乡土中国,使之成为一个硕大的“拟制的家”。(101)以此观之,四大门宗教支配的仙家-香头谱系,同样是乡土中国拟亲属文化特质的有效载体。反之也可以说,经由香头运行的四大门宗教是“建立在家族主义”之上的。(102)人神同体的香头不但扮演了信众日常生活指导者、家庭保护者、个体生命呵护者、社区秩序维护者等多种角色,在进香朝顶等群体性敬拜活动中,他还是社会关系抑或说“权力的文化网络”(103)的多元核心之一。
其二,“家庭宗教”之说。在其论文的结论部分,陈永龄随意的使用了“家庭崇拜/宗教”来指称其论文在“村内的宗教活动”一节中描述的发生在“家庭中的宗教崇拜”,包括祭祖与祭神。(104)虽然陈永龄在其一直未正式刊载、出版的学位论文中并未对该术语进行深度阐释和学理分析,且是在最后信手拈来式的随性使用,但“家庭宗教”的明确提出,在学术史中却意义非凡。1949年,在其名著《祖荫下》之中,许烺光也使用了“家庭宗教(family religion)”一词,尽管它并非是许烺光学术帝国的关键词,而且内涵、外延和陈永龄的使用也有不同。对许烺光而言,家庭宗教的核心就是祖先敬拜。他指出,西镇的祖先敬拜是一种日常化的行为,“家庭是宗教的一部分,反之宗教也是家庭的一部分”,奇迹、灵验并非家庭宗教之关键。(105)异曲同工的是,作为重要的比较神学家,裴玄德(Jordan D.Paper)一直强调基于家的宗教对人类宗教和文明的重要意义。为此,他认为中国的敬祖,即家庭主义(familism)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也是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以此为基础,裴玄德创建了与基督教认知范式并驾齐驱的认知人类宗教的新范式,即Chinese Religion。(106)
其三,“家务事”之说。至今,诸多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都在试图回答为何是女性居多这一事实。这些回答多取径于后现代,尤其是女权主义的视角,进行由果溯因,以今审古式看似合理的分析,即常将女性亲近神灵归因于男权的禁锢与压迫而寻求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一种表达。(107)然而,正如平郊村研究所呈现的那样,拜神信佛的女性居多在相当意义上是因为供奉神佛是家务事的一部分,因而是“女子传统的当然的任务”。(108)显然,如果没有长期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和考现,即有着过程与行为的视角,是很难看到供奉神佛的“家务事”属性的。事实上,当下的经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七十多年前对供奉神佛家务事属性认知的合理性。(109)
最后,在当年燕大诸多学生撰写的民俗学志中,“宗教”与“仪礼-礼俗”的分野是明显的,尽管描述的事实多有交集。如果将宗教广义地定义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联,和人类对生命、宇宙以及万物的思考与终极关怀,那么指向人生仪礼的传统礼俗、与自然交流的岁时节庆,显然也可心安理得地划分到宗教的范畴。正是在此意义上,日本学人架构的“民俗宗教”早已将这两部分纳入了其研究的范畴,(110)中国学人也开始正视家与庙之间相互让渡的辩证关系,(111)强调在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庙庆、朝山中指向人生仪礼相关仪式的核心性。(112)
①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7页。
②Gamble,Sidney D.,Peking,A Social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1.
③杨燕、孙邦华:《许仕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推进》,《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68-75页。
④许仕廉:《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三卷(1929),第180页。
⑤Fei,Hsiao-Tung,Forward,in Hsiao-Tung Fei & Chih-I Chang,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48,p.ix;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47-48、212-214页。
⑥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1936),第123页。
⑦陈聚科、庐铭溥、余即荪:《前八家村社会经济概况调查》,《清华周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1935),第41-50页。
⑧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第107-116页。
⑨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第151-205页。
⑩岳永逸:《忧郁的民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33页。
(11)限于篇幅,“民俗学志”的定义将专文另述。
(12)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第99-100页。
(13)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53、83-106、166-171、307-316页。
(14)参阅廖泰初:《一个城郊的村落社区》,1941,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铅印本;《沦陷区的一个城郊社区》,《华文月刊》第二卷第2-3期(1943),第58-62页。
(15)诸如:周廷燻:《一个农村人口数量的分析》(1940);沈兆麟:《平郊某村政治组织》(1940);方大慈:《平郊村之乡鸭业》(1941);韩光远:《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1941);刘秀宏:《前八家村之徐姓家族》(1947);蔡公期:《平郊村农工之分析》(1947);杨景行:《平郊村一个手工业家庭的研究》(1948);张绪生:《平郊村学龄儿童所受的教育》(1948)和马树茂:《一个乡村的医生》(1949),等等。
(16)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第110页。
(17)同上,第109页。亦可参阅《社会科学各系工作报告·社会学系》,《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第240页。
(18)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第99页。
(19)黄华节:《怎样研究民间宗教》,《民间》第一卷第十期(1934),第13-18页;《定县巫婆的降神舞》,《社会研究》第一○五期(1936),第437-441页。
(20)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88-92、97-99页。
(21)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6页。
(22)李慰祖:《四大门》,第3-4页。
(23)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5页。
(24)蔡公期:《平郊村农工之分析》,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7,第3-4页;杨景行:《平郊村一个手工业家庭的研究》,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8,第3页。
(25)Nedostup,Rebecca Superstitious Regimes: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26)岳永逸:《朝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9-181页。
(27)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07-171页。
(28)B.Malinowski:《文化论》,费孝通、贾元荑、黄迪合译,《社会学界》第十卷(1938),第183页。
(29)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7页。
(30)同上,第1页。
(31)同上,第4-5、85-102页。
(32)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9页。
(33)同上,第1页。
(34)同上,第1-2页。
(35)同上,第3-4页。
(36)同上,第106、109页。
(37)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11页。
(38)于鹤年:《民俗学与神马》,《河北月刊》第四卷第三期(1936),第2-3页。
(39)韩光远:《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48页。
(40)马树茂:《一个乡村的医生》,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9,第39-53页。
(41)权国英:《北平年节风俗》,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0,第28-33页。
(42)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页。
(43)权国英:《北平年节风俗》,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0,第11-20页。
(44)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6、20-30、43-46页。
(45)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4页。
(46)Harrell,Steven."Belief and Disbelief in A Taiwan Village",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4,pp.104-120.
(47)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9页。
(48)同上,第48、83-84页。
(49)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46、69、103-105页。
(50)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52-55页。
(51)同上,第56-76、131-133页。
(52)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87-196页。
(53)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72页。
(54)同上,第102页。
(55)同上,第37、43页。
(56)Kang,Xiaofei."In the Name of Buddha:the Cult of the Fox at a Sacred Site in Contemporary Northern Shaanxi",《民俗曲艺》,138(2002),pp.67-107.
(57)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81页。
(58)奉宽:《妙峰山琐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
(59)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
(60)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474页。
(61)岳永逸:《保守与激进:委以重任的近世歌谣》,《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100、102页。
(6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83-284、288页。
(63)岳永逸:《朝山》,第263-265页。
(6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第284页。
(65)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475页。
(6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39-40页。
(67)顾廷龙:《妙峰山进香调查》,《民间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33),第91-104页。
(68)当然,这种心性不仅仅是顾颉刚个人的,而是社会学的方法、局内观察法没有切实运用于民俗调查的他那个时代学界的共性,这种低姿态走向民间实则俯视的余波至今犹存。对此的系列反思与批判,参阅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4、243-255、320-339页;《朝山》,第1-32页。
(69)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6期,第36-39页。
(70)奉宽:《妙峰山琐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第94页。
(71)同上,第28页。亦可参阅燕归来簃主人:《北京妙峰山纪略·中道》,《新东亚旬刊》第一卷第十八期(1939),第24页。
(72)王文光:《天津的妙峰山进香情形》,《京报副刊》第251号(1925),第7-8页。
(73)燕归来簃主人:《北京妙峰山纪略·北道》,《新东亚旬刊》第一卷第十九期(1939),第23-24页。
(74)燕归来簃主人:《北京妙峰山纪略·中北道》,《新东亚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1939),第25页。
(75)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第176页。
(76)周振鹤:《王三奶奶》,《民俗》第69-70期(1929),第70-71页。
(77)奉宽:《妙峰山琐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第8、88-89页。
(78)顾廷龙:《妙峰山进香调查》,《民间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33),第100、98页。
(79)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页。
(80)周振鹤:《王三奶奶》,《民俗》第69-70期(1929),第105-106页。
(81)Ward,C.A.,Spirit Possession and Mental Health:A Psycho-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Human Relations,vol.33,no.3(1980),pp.146-163.
(82)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72-74、102-108页。
(83)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5-20页。
(84)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82-83页。
(85)同上,第83-84页。
(86)同上,第103页。
(87)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5页。
(88)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89)Kang,Xiaofei.The Cult of the Fox:Power,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143.
(90)Ibid.,pp.145-146.
(91)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06-107页。
(92)李有义:《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36年,第133页。
(93)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51、53页。
(94)Li,Wei-tsu."On the Cult of the Four Sacred Animals(Szu Ta Men四大门)in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Folklore Studies,vol.Ⅶ(1948),pp.1-94.
(95)李慰祖:《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96)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21-123页。
(97)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42页。
(98)同上,第125页。
(99)同上,第50、140页。
(100)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1)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14-219页。
(102)李慰祖:《四大门》,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45页。
(10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04)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8-12、103、105页。
(105)Hsu,L.K.,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9,p.242.
(106)Paper,Jordan D.,The Spirits Are Drunk: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Relig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61-68;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Religion,"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Taipei],vol.1,no.1(2013),pp.1-32.
(107)Hsu L.K.: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p.27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84页;Sangren P.S.,"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Kuan Yin,Ma Tsu,and the ‘Eternal Mother’," Signs 9(1983),pp.4-25; "Myths,Gods,and Family Relations," in Shahar,Meir and Robert P.Weller(eds),Unruly Gods: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pp.150-183。
(108)陈涵芬:《北平北郊某村妇女地位》,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0,第44页。亦可参阅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第14页。
(109)Bunkenborg,Mikkel."Popular Religion inside out:Gender and Ritual Revival in a Hebei Township".China Information,vol.26,no.3(2012),pp.359-376.
(110)[日]宫家准:《日本的民俗宗教》,赵仲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1)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310-316页。
(112)华智亚:《人生仪礼、家庭义务与朝山进香:冀中南地区苍岩山进香习俗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第89-98页;岳永逸:《朝山》,第268-2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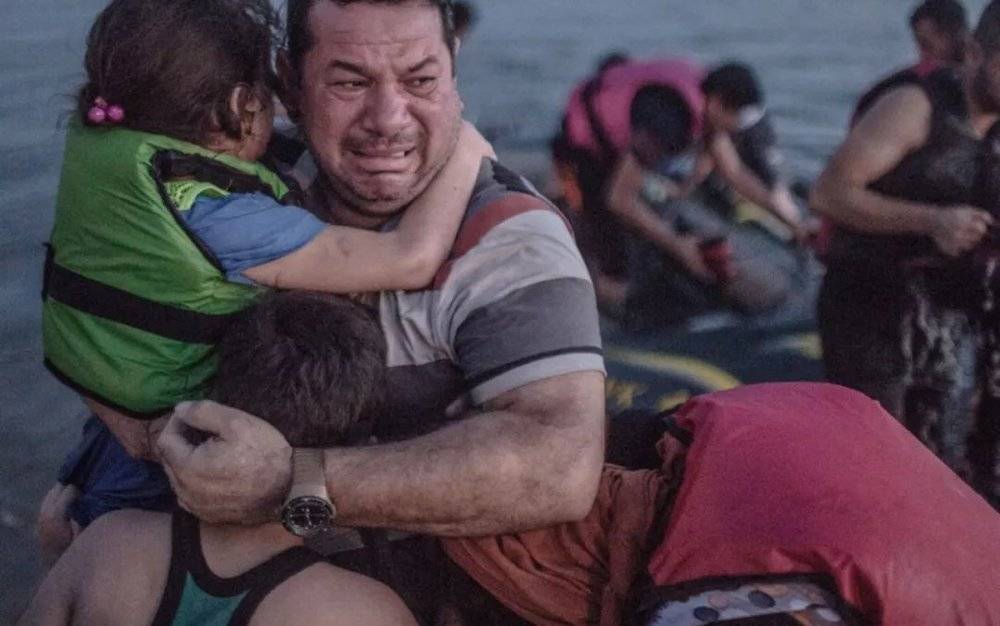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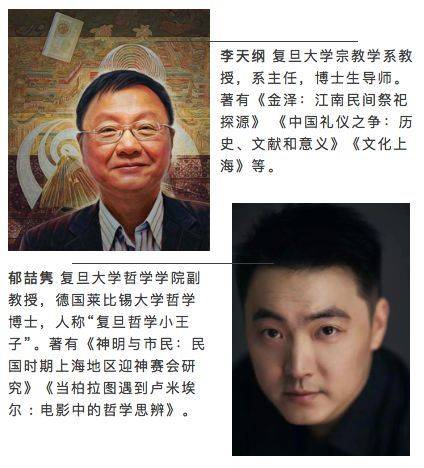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